过渡的那一分钟,我刚抬起脚要穿到马路的另头。午夜走路好处是,没有很多人塞在我的视野里,我可以认真哈一口冷气,然后在建筑与建筑的空隙里提问和嚎叫。跨年的意义在于加上意义,时间的量度是人类的行为。
那天也是腊八,早上就着两杯可乐吃了五个汤圆。在床上给娜嘉发了条短信,她告诉我她的敬酒服是“金子色的晚礼服和大红的鱼尾裙子”,我不会说客套话,只是一直说要开心和顺利。
恐惧感从每个细小的地方渗透进来,它顺着窗帘滑动的声响灌入我耳膜,从无法关闭的水喉滴进我的皮肤,更甚是它在我每一节律呼吸里散成无数微小因子循环着进入我的身体。与情绪对抗将对时间感知无限拉长扭曲,导致我认为睡觉是最快的度日办法,并开始贪图睡醒时短暂的失忆及感官的模糊。我的思维裹足了我,绞干了我余下自诫因子,然后在脑子里投下沉闷的声响。
之后是平抑,像是跟一个顽童做抗争。他想吃一颗糖,而商店关门了,你给他同样的糖,他朝你尖叫撕扯头发,因为他就只要商店里卖的。重点不在糖,也不在顽童,在关了门的商店。但我还是平抑了。像射过精的男人,花了两小时前戏抽插,花了一秒射精,射精完了就得收拾衣服出门上班,选吃什么做早餐,猜测在六渡桥会不会堵车,报告的英文拼字有没有错漏这些老俗的问题。老俗的问题总是绵长的,容易消抵精神。
但我还是缺一双手,这是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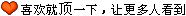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