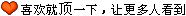完成几个脑筋急转弯,总算有时间来个上周末的活动回顾。因为前段时间朋友提到凤凰岭的杏花和大觉寺的玉兰,期待放风的我一直“耿耿于怀”,不去一趟就放不下,早早的就开始憧憬了。
周六阳光明媚,正是出游的好天气。从通县驱车前往凤凰岭,这段路途可不近。头一日问同事,问老哥,希望他们能指点迷津,把得来的路线图发到手机中,以便路上参考。可没想到,几个路盲上了路之后,一到岔路口就不知该如何抉择。搞笑的两次记录在此记下,以示警醒:
1、 认为自己挺明白的我,因为失误,竟然让队伍踏上归途。那种感觉,好像过家家,当玩游戏呢……
2、 按照指示牌方向,不知怎地还是转到五环上了,结果在肖家桥岔口处,明明看着北清路的大牌子,还犯嘀咕:究竟往哪里走呢?因为前面的一次失误,路盲们讨论后决定,停靠路边,打电话远程咨询一下。不过,我们因此还成为引路人了。没想到后面还有个步我后尘的,停下车来向我们问询方向……
我若是哲人,想必又得对此大发感想了。
最后电话咨询的结论是:别再往前走了,问问附近的人吧。于是谨慎地踏上北清路。当前面的指示牌上赫然显示“凤凰岭”几个字时,我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带来的惊喜。沿着指示方向前行,沿途处处花儿盛开,还看到不少蜜蜂采蜜。尤其是在正对西山前行的时候,特别惬意。此种情景竟然让我感受到南国的春天了,整个大自然似乎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淡绿、翠绿,各种颜色的层次感鲜活地呈现在眼前。没有了冬天的沉重,心情自然随之轻松起来。
在北京难得看山,这里的石山也算养眼了。只可惜,杏花节里没有杏花,我们现在去的时间已经晚了。最晚时间也是在4月初。:(

上凤凰岭的途中,见这一大块石头,心想逆光拍摄可能还会有那么一点意境。

西山的石头长得还是颇有特色,只要你想,也可随便给这处那处编出个什么景点来。这一排石头,像极了教堂里的人整齐列队,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平安。

天工巧匠将作品遗忘于大自然了,石头上似乎还有着踏过的足迹。

这张像什么,尽管想像吧。

色彩与线条的自然组合,天空与大地的完美融合。

去凤凰岭的路上,还有去阳坊的路边,经常能看见这些成片成片的紫色小花,颇有普罗旺斯薰衣草的味道。这里似乎没有人工的痕迹,第一眼看见这近乎原生态的景色时,我的分贝值最高。
停车坐爱紫花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车子停靠路边,我和朋友径直跑过去,恨不得将这所有都揽入自己的怀中,小心地留影拍照,生怕自己会贱踏了这些小生命。

中午去了阳坊,吃久闻盛名的正宗阳坊涮肉。还是认为北方菜再怎么好吃,也比不过南方的菜精致耐回味。
由于天生的亲水性,见到阳坊边的运河就忍不住要去看看。当时风很大,几乎要推着我们走了。但照片拍出来,看这些树和水,似乎还是风和日丽。

花开红艳艳。

在大觉寺里的一大遗憾,就是玉兰节也同样是没有玉兰花看了。寻寻觅觅找到的玉兰树,让我失望至极。只有几片凋零的花儿,看上去还很肮秽。好在这里还有自己多年没看过的梨花。满树的梨花,让我想起童年。

一排绍兴酒,就摆在门前。想来能吸引过去的,不知是不是都是好酒之徒。

帖子发出后,有人指点,这片紫色的花海是二月兰。从此不会忘记。
| 二月兰 |
| 作者:二月兰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0-16 文章录入:世外园林 责任编辑:世外园林 |
|
别名: 菜子花 诸葛菜 科名: 十字花科 拉丁名: Orychophragmus violaceus 生态习性 耐寒性强,冬季常绿。又比较耐阴,适生性强。从东北、华北,直至华东、华中都能生长。冬季如遇重霜及下雪,有些叶片虽然也会受冻,但早春照样能萌发新叶、开花和结实。对土壤要求不严。紫色花,从下到上陆续开放,2~5、6月开花不绝,尤其是群栽时,一片蓝紫色。 形态特征
繁殖培育 繁殖方式以种子播种为主,8~9月直播 园林用途 二月兰是中国北方土著物种,花期长,花色淡雅,且本物种性耐寒旱、耐贫瘠,繁殖能力强无需专门养护,因而中国北方的一些园林、公园,如北京的天坛公园,在园内绿地人工收集和散播二月兰的种子,以形成二月兰花海的效果。在北京的郊区,五环路的路基和一些河道的护坡,园林部门也人工播撒二月兰等植物的种子,以进行绿化。 另外因早春花开成片,为良好的园林阴处或林下地被植物,也可用作花径栽培。在园林绿地、林带、公园、住宅小区、高架桥下常有种植,作为观花地被广泛应用。公园、旅游景点所采用。专家还建议在机场成片种植二月蓝,不仅冬天披绿,春天紫花成片,而且它能延续自繁,毋需过多养护,能与其他植物混种,是集多种优点于一体的好品种。 产地分布 二月兰原产于中国东部,常见于东北、华北等地区,分布于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四川、上海等省份,野生或人工栽培。由于本物种在部分地区由人工引种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因而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本物种的分布范围。 二月兰
季羡林(1911—),山东清平人,学者、翻译家、散文家。著有学术论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译作《沙恭达罗》(迦梨陀娑)、《罗摩衍那》(印度古代民间叙事长诗),散文集《天竺心影》等,有《季羡林文集》行世。 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如果只有一两棵,在百花丛中,决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它却以多胜,每到春天,和风一吹拂,便绽开了小花;最初只有一朵,两朵,几朵。但是一转眼,在一夜间,就能变成百朵,千朵,万朵。大有凌驾百花之上的势头了。 我在燕园里已经住了四十多年。最初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种小花。直到前年,也许正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我蓦地发现,从我住的楼旁小土山开始,走遍了全园,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我在迷离恍惚中,忽然发现二月兰爬上了树,有的已经爬上了树顶,有的正在努力攀登,连喘气的声音似乎都能听到。我这一惊可真不小:莫非二月兰真成了精了吗?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二月兰丛中的一些藤萝,也正在开着花,花的颜色同二月兰一模一样,所差的就仅仅只缺少那一团白雾。我实在觉得我这个幻觉非常有趣。带着清醒的意识,我仔细观察起来:除了花形之外,颜色真是一般无二。反正我知道了这是两种植物,心里有了底。然而再一转眼,我仍然看到二月兰往枝头爬。这是真的呢?还是幻觉?一由它去吧。 自从意识到二月兰存在以后,一些同二月兰有联系的回忆立即涌上心头。原来很少想到的或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现在想到了;原来认为十分平常的琐事,现在显得十分不平常了。我一下子清晰地意识到,原来这种十分平凡的野花竟在我的生命中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我自己也有点吃惊了。 我回忆的丝缕是从楼旁的小土山开始的。这一座小土山,最初毫无惊人之处,只不过二三米高,上面长满了野草。当年歪风狂吹时,每次“打扫卫生”,全楼住的人都被召唤出来拔草,不是“绿化’,而是“黄化”。我每次都在心中暗恨这小山野草之多。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把山堆高了一两米。这样一来,山就颇有一点山势了。东头的苍松,西头的翠柏,都仿佛恢复了青春,一年四季,郁郁葱葱。中间一棵榆树,从树龄来看,只能算是松柏的曾孙,然而也枝干繁茂,高枝直刺入蔚蓝的晴空。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注意到小山上的二月兰。这种野花开花大概也有大年小年之别的。碰到小年,只在小山前后稀疏地开上那么几片。遇到大年,则山前山后开成大片,二月兰仿佛发了狂。我们常讲什么什么花“怒放”,这个“怒”字下得真是无比地奇妙。二月兰一“怒”,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东坡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是花们好像是没有什么悲欢离合。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么悲与喜。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人这个万物之灵却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欢。这真是多此一举,然而没有法子。人自己多情,又把情移到花,“泪眼向花花不语”,花当然“不语”了。如果花真“语”起来,岂不吓坏了人!这些道理我十分明白。然而我仍然把自己的悲欢挂到了二月兰上。 当年老祖还活着的时候,每到春天二月兰开花的时候,她往往拿一把小铲,带一个黑书包,到成片的二月兰青草丛里去搜挖荠菜。只要看到她的身影在二月兰的紫雾里晃动,我就知道在午餐或晚餐的餐桌上必然弥漫着荠菜馄饨的清香。当婉如还活着的时候,她每次回家,只要二月兰正在开花,她离开时,总穿过左手是二月兰的紫雾,右手是湖畔垂柳的绿烟,匆匆忙忙走去,把我的目光一直带到湖对岸的拐弯处。当小保姆杨莹还在我家时,她也同小山和二月兰结上了缘。我曾套宋词写过三句话,“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往往在二月兰丛里看到她们: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 所有这些琐事都是寻常到不能再寻常了。然而,曾几何时,到了今天,老祖和婉如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小莹也回了山东老家。至于虎子和咪咪也各自遵循猫的规律,不知钻到了燕园中哪一个幽暗的角落里,等待死亡的到来。老祖和婉如的走,把我的心都带走了,虎子和咪咪我也忆念难忘。如今,天地虽宽,阳光虽照样普照,我却感到无边的寂寥与凄凉。回忆这些往事,如云如烟,原来是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灵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对于我这样的心情和我的一切遭遇,我的二月兰一点也无动于衷,照样自己开花。今年又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在校园里,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霄汉,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这一切都告诉我,二月兰是不会变的,世事沧桑,于她如浮云。然而我却是在变的,月月变,年年变。我想以不变应万变,然而办不到。我想学习二月兰,然而办不到。不但如此,她还硬把我的记忆牵回到我一生最倒霉的时候。在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老佛爷”,被抄家,被打成了“反革命”。正是在二月兰开花的时候,我被管制劳动改造。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到一个地方去捡破砖碎瓦,还随时准备着被红卫兵押解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坐喷气式,还要挨上一顿揍,打得鼻青脸肿。可是在砖瓦缝里二月兰依然开放,怡然自得,笑对春风,好像是在嘲笑我。 我当时日子实在非常难过。我知道正义是在自己手中,可是是非颠倒,人妖难分,我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一腔义愤,满腹委屈,毫无人生之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成了“不可接触者”,几年没接到过一封信,很少有人敢同我打个招呼。我虽处人世,实为异类。 然而我一回到家里,老祖、德华她们,在每人每月只能得到恩赐十几元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殚思竭虑,弄一点好吃的东西,希望能给我增加点营养;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希望能给我增添点生趣。婉如和延宗也尽可能地多回家来。我的小猫憨态可掬,偎依在我的身旁。她们不懂哲学,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视我为异类,她们视我为好友,从来没有表态,要同我划清界限。所有这一些极其平常的琐事,都给我带来了无量的安慰。窗外尽管千里冰封,室内却是暖气融融。我觉得,在世态炎凉中,还有不炎凉者在。这一点暖气支撑着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没有堕入深涧,一直到今天。 我感觉到悲,又感觉到欢。 到了今天,天运转动,否极泰来,不知怎么一来,我一下子成为“极可接触者”。到处听到的是美好的言词,到处见到的是和悦的笑容。我从内心里感激我这些新老朋友,他们绝对是真诚的。他们鼓励了我,他们启发了我。然而,一回到家里,虽然德华还在,延宗还在。可我的老祖到哪里去了呢?我的婉如到哪里去了呢?还有我的虎子和咪咪到哪里去了呢?世界虽照样朗朗,阳光虽照样明媚,我却感觉异样的寂寞与凄凉。 我感觉到欢,又感觉到悲。 我年届耄耋,前面的路有限了。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叫《老猫》,意思很简明,我一生有个特点:不愿意麻烦人。了解我的人都承认的。难道到了人生最后一段路上我就要改变这个特点吗?不,不,不想改变。我真想学一学老猫,到了大限来临时,钻到一个幽暗的角落里,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人世。 这话又扯远了。我并不认为眼前就有制定行动计划的必要。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我的健康情况也允许我去做。有一位青年朋友说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话极有道理。可我并没有全忘。有一个问题我还想弄弄清楚哩。按说我早已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年龄,应该超脱一点了。然而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还有一件心事:我想弄清楚,什么叫“悲”?什么又叫“欢”?是我成为“不可接触者”时悲呢?还是成为“极可接触者”时欢?如果没有老祖和婉如的逝世,这问题本来是一清二白的。现在却是悲欢难以分辨了。我想得到答复。我走上了每天必登临几次的小山,我问苍松,苍松不语,我问翠柏,翠柏不答。我问三十多年来亲眼目睹我这些悲欢离合的二月兰,她也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