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翻桌子找东西,顺手看了看中学时的日记,觉得那个时候真是傻得可爱,当时除了物理,我最喜欢的是文学,而且爱好广泛,从古诗词到现代诗都很喜欢,考上大学后,还是很喜欢文学,惊叹学校图书馆的藏书(现在看来其实藏书不算多的),天天到图书馆里借书读。直到碰到现在的老婆,我才知道自己的文学天赋差多远,对我的文学梦造成彻底打击,以后再也不舞文弄墨,专心学习计算机了。
不过看看中学时写的文字,还挺有意思,那个时候对自然的关注远远多于对社会的关注,所以心灵很纯净,文字也很纯净,好象远比现在的思想境界高。下面是1990年8月15日写的一篇日记(当时16岁,高二暑假),摘录如下:
八月十五 三 雨

清晨睁不开眼,便听到哗哗的雨声。昨天害眼了,什么也没干,这是我第一次害眼,长这么大,除了把眼睛弄近视外,还没尝过害眼的滋味,好难受!
揉开一条缝,眯着眼用清水洗了又洗,一照镜子,把嘴都气歪了,这是胡海吗?眼睛红红的,一丝精神也没有,呆呆地象死了。这也没办法呀。
出门一下,置身风雨中,凉丝丝的,偶尔有几滴斜打在胳膊上,更有一种凉电般转给大脑。雨水比初起床时小了许多,细细的,只看清前面的几条,再往远就只见灰蒙蒙一片。不由想起以前在一本摄影书上看到几幅小雨的照片,觉得远不是那回事。一点雨的样子也没有,只是模糊成一片,一点也不成功。我想只有在风雨中,感到那片凉,听到那哗哗声,眼前弥漫丝丝雨线。呼吸着清新的气息,才会感到雨味。只凭视觉,根本无法体会那粼粼的清雨。
打着伞,总和雨有一丝界限。不由想起和冯一起淋雨的畅快!那是麦假的开学,或者是期中考试后开学吧,才到校,没事可做,晚自习我们溜出去,那时便下了小雨,跑到大众,淋了个湿透,看一场投影,深夜赶回,雨不知大了几倍,到寝室时,衣裳象洗过一样,拧了半个小时,第二天都没干。
坐在窗前,闭上眼,听那冷冷雨。这一阵子过去了,大概连细雨也没有了吧。周围静了许多,听得见偶尔树上的雨滴到水面的声音,什么响声呢?形容不出,只好说“啪”地一声,其实一点也不像。古人写雨的不少,“留得残荷听雨声”、“雨滴梧桐”、“中年听雨客舟中”……到底雨声是什么样,没有人写。他们好聪明,只把那种形象说出来,让你自己品位,去感受那无边无际的雨。心里产生无限思绪,又加之雨,可是却无法用语言表示。人们在雨天有种独特的感受,却又没办法记下,只会留在记忆中。一种朦胧模糊的美,又记得,又记不得,雨的迷人应是在于此吧。
想了这么多,用什么来表示这种声音呢?不如自己造个字,没有人知道它念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只属于胡海。好好想想……有了,写作“口雨洼”,当然是雨滴到水洼的声音,念时不用声带发音,嘴唇合在一起再分开,就是这个声音,一点不错,哈,挺不错!
可是只想出这一种声音,象刚才风吹树叶的声音,再刚才雨打树叶的声音,都是说不出的,还有那么多雨点滴到地上,水流成河后,又打在水上,只用“哗哗”这个词,显得多么贫乏。
不知人们为何如此重视视觉,而又轻视听觉呢?纵然听觉次要,可也不能置之不理,总有一天人类耳朵全退化了,又把眼睛都搞近视,看怎么戴眼镜?
又想起《老残游记》里的那篇文章,把声音全转成视觉,写得好有水平,不知道哪个人发明的移觉这个修辞方法,我对他五体投地,斗转星移,好棒!
雨又大起来,比刚才还大。坐在门前,听得见前面操场里一片哗哗声,象千军万马在奔腾,象……(看来我的移觉水平够差的),总之,这阵喧哗声又感染了我,又仿佛置身到大雨中。随手关上门,竟发现把雨声隔开了,好象那声音从另一个世界传来,低沉而飘渺。走到里间,听到的竟是另一种声音,屋后的实验室院长满了桐树,雨打在树叶上,沙沙地,声音又低了,却充满灵气。真高兴,一会儿把门打开,又把门关上,跑到里屋,又跑出来,再关门,再进去……我怎么也停不住脚,被我的发现感动得又高兴又没法说。
因为害眼,所以尽量用耳朵听,才发现世界上竟还有一个如此美丽的地方。可是正因为害眼,又觉得如果只凭听觉,是多么有限!一个人如果瞎了,真不知道他怎么活,没有眼睛的世界是一滩死水!真佩服那些盲人,特别是后天的,他们好坚韧,若有如此的生命力,又有何坚不催。
下午又无事听雨,在停雨时分,竟听到蝉叫。我感触很深,柳永那首广为人知的词“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以前虽觉得美,却不大相信。天气渐寒,蝉应该没了吧,而雨后这么凉的天气,它怎么会叫呢?现在我当然信服了,冷冷湿气,几声蝉鸣,黄昏雨后时分那无涯的寂寥,怎不是一种凄楚的美。
要不是眼疼,我会写很多,因为闭上眼睛,便只有听觉了。难得有这么一天,啊,这难得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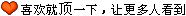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