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叶
作者:蓝缕
所有的叶子里,枫叶是最美丽的。
他只是自顾自地深情地红着,却不知有人在为他颠狂。那是柳絮,一个夏日的颠狂者,却在秋日的萧瑟里,随风而去。
红是红地热烈,即便辗转秋风里,兀自溢着生气,而纤细的柳枝,只能在昏昏然的天气里,摆动她的腰肢,她想告诉别人什么呢?
柳儿千百度地兴叹,她渴求能见上红叶一面,可,他们实在是无法并世而存的。
红叶舞秋山,偌大一个山谷里,漫山遍野的就只是红叶,他沉溺在自己的美丽里。他不知道就在不久之前,在那河泽之畔,有人为他寸寸而折。他不曾要求什么,他一生都只呆在这山谷里,呆在自己的世界、一个只有他的世界里。他总认为,这里,便是世上最可爱的所在了。除了这空旷的山谷,除了他自己,他的眼里,便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
红叶哟,那动人的风姿、那片片的深情、还有那倘着孤傲的血液的脉络,在风起时,低诉着秋的景致。这一生,他的所闻所见,只有这秋,而他的心里,也是只有这瑟瑟之秋。
没有人明白他,人们见到的,总是那生气盎然而又浓烈如火的他,有谁知道,在他的脉络里流淌着的,除了那份孤傲,更有一份深深的寂寞。孤是与生惧来的,而这寂寞,却是他所甘愿。
没有人知道,连柳儿都不曾知道。这对于她,是一种悲哀,而对于他,则更是一种侵浸入髓的悲哀。
柳儿企图让时光快些过去,好在那秋日,见他一面。时光是逝去了,经霜的红叶,愈加艳地动人,而她自己,却已无存;时光又逝去了,等她再来时,红叶又无存。
纵生生世世,都奈何是无缘。
红叶随风舞,风中,仿佛有他低诉的声音;柳絮寸寸折,河畔,仿佛有她醉意的叹息……
——一九九七.十.十一.
久久的寂寞啊,或许已经习惯了。那深情的红叶,终究是有柳絮遥遥地伴着他。
颠狂柳絮随风去,深情红叶逐水流。但愿,柳絮入泥,红叶坠地,好相聚在尘俗里……
——蓝缕
————————————————————————————————————————
斜阳劫
序
引《情叶》于《斜阳劫》之前,并不是两者有什么关系。《情叶》是《情叶》,《斜阳劫》是《斜阳劫》,二者毫无关联可言。
“但愿,柳絮入泥,红叶坠地,好相聚在尘俗里……”这句话,是我将《情叶》引于《斜阳劫》之前的最直接的原因。有种感觉,《斜阳劫》仿佛就是柳絮与红叶在尘俗里的相聚的传奇。然而,《斜阳劫》里其实是没有人可与那般凄艳的柳絮与红叶比拟的。
将《情叶》引于《斜阳劫》前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斜阳劫》是为某个人而写的。
《斜阳劫》构思于三年前,但一直以来都只有个隐约的框架,连主要人物,也仅有一个名字。如果不是认识了这个人,或许再过三年,它也依然苍白如初。
这个人,可以认为便是使柳絮寸寸而折的红叶。
“颠狂柳絮随风去,深情红叶逐水流。”
但,那遥遥地伴着红叶的柳絮,不是我。
九八.一.九
请鸿轩
第一章
日暮,斜阳千里,彤云如火。
秋海蔚在斜阳里,“斜阳阁”的斜阳里。
与其说他喜欢斜阳,不如说他对一切带着“斜阳”这两个字的事物,都有种特殊的亲近之心。比如他来这家掌柜稀里糊涂,伙计没精打采,厨师马马乎乎的“斜阳阁”酒楼,就纯粹为了那个名字。
他喜欢“斜阳”这两个字,因为,有一个女子,名叫李斜阳,李斜阳手中有一股力量,是为斜阳堂。
“斜阳阁”的生意素来清淡,来这儿的人通常都不是为了吃饭。秋海蔚是为了它的名字,靠窗的一桌客人则十有八九是图它的清静。秋海蔚来的时候,他们便已经在那里了,四个人,三男一女,桌上放着纸、墨、笔、砚一应文房用具,那女子执笔,一男子磨墨,一男子捧纸,一男子替她翻查着什麽,四个人神情都很凝重,桌角上的几盆菜,始终没有动过。
那女子落笔极快,秋海蔚进来没多久,就看她换了有十几张纸,纸上写什么虽看不清楚,却可以大致看出满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
终于,她长吁了口气,放下笔,向那磨墨的男子道:“《胜传烽传》的底稿我起好了,七哥,接下来就看你的了。离夏至还有三天,给你润色修改总够了吧?”
那男子也吁了口气,展颜笑道:“就算明天是夏至也没关系,九妹的文字,还用得着我来改吗?”
“九妹”摇了摇头,“七哥取笑了。……只是,这篇传文语焉不详的地方太多,我看我们还是再参详一下的好。”
“七哥”沉吟了一下,拿过那篇文章,小声读了起来:“胜传烽,不知何许人也,有问之者,含糊以塞。或曰,胜传烽者,武当故剑客胜箫也。然询其何故别武当而入斜阳,则瞠目不知所对。探乎武当众侠,闻胜箫之名,立缄口,偶于江湖邂逅,辄侧目过,传烽亦冷笑不语。”
他住了口,想了想,“你在学《五柳先生传》么?胜传烽的来历,就这样算交代了?”
那翻查的男子接口道:“没办法,胜传烽的来历我和三哥怎么查也查不出来,连李斜阳都说不知道。”
捧纸的男子补道:“我曾经偷入过武当去查胜箫的资料,可是武当有关胜箫的一切记录都被销毁了。”
“七哥”挑了挑眉,“你们有没有去问过胜传烽本人?”
三人互相看看,同时摇了摇头。
“七哥”正色道:“‘神谷’写侠史,求的是秉笔直书,以往为已故者作传,引用传说,那是没办法,但胜传烽不是死人,他既然活着,不管他肯不肯说,你们都该去问问。这点道理,九妹刚开始编修武林史不知道,难道三哥四哥你们也不知道么?”
“三哥”“四哥”对视一眼,垂下了头,“九妹”则很爽快地道:“那,我明天就去斜阳堂见胜传烽。”
“七哥”点了点头,又接着念下去:“其于斜阳堂,位仅李斜阳之下,李倚重之,事无巨细,俱与商,达旦不以为异,并肩出入不以为怪,时遭非议。久之,人习为常,遂息。”
“四哥”冷笑一声,“九妹写得也太客气了,李斜阳和胜传烽私通,谁不知道?他们自己都不瞒着别人,你又何苦为他们遮遮掩掩的?”
从他们提到胜传烽这个名字起,秋海蔚就一直留神在听他们的对话,胜传烽和李斜阳的传言,他当然也听说过。现在,听到连“神谷”的人都这么说,他心里不由一阵绞痛,别人可能会胡说,可是,“神谷”的人,却绝不会胡说。
胜传烽,胜传烽是何许人也,秋海蔚心中暗下决心,他定要见识见识。
正在此时,“斜阳阁”又来了一个人,一个三十上下的少妇。
这少妇一身缟素,鬓边一朵白花,脸上冷冰冰的毫无表情,进门就朝秋海蔚而来。
秋海蔚见到她,脸色刹时变得很难看。
她在他桌前站定,先冷冷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又扫了眼四周,方道:“你眼里若还有我,就随我来。”她的声音也平平板板的,不带一丝感情。
秋海蔚缓缓站起身,缓缓道:“小弟敢不从命。”
少妇二话不说,转身向外走去。
他们走了,“三哥”忽然道:“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
闻言,“四哥”会心地一笑,“七哥”漠不关心地继续翻看着《胜传烽传》的底稿,“九妹”则饶有兴趣地问:“是谁?”
“三哥”得意地笑道:“那男的就是秋海蔚……”
“九妹”一惊,“秋情不绝系斜阳,无奈潇湘向胜郎?”
“三哥”愕然反问:“你在说什么?”
“九妹”道:“怎么,你不知道?这是舒家三姐的《秋水长天阁序》里的呀!秋水长天阁三个大弟子,再加上武当胜箫,所有的纠葛都在这两句诗里,是全文的点睛之笔,你难道没看过吗?”
“三哥”尴尬地笑笑,“我对舒家姑娘写的诗文不感兴趣……”
“四哥”“嗤”地笑了一声,道:“你对人家的诗文不感兴趣,那人家的人呢?”
“三哥”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你……”
“九妹”忙道:“你们别吵!三哥,那男的是秋海蔚,那女的又是谁?”
“三哥”道:“那女的?你不知道?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九妹”眼珠一转,“啊,她就是秋水长天阁的大弟子,秋海蔚和李斜阳的师姐容潇湘?”
“四哥”颔首道:“不错,她就是胜箫的妻子。我和三哥还特地找过她……这女人好凶!”
城外山冈上,荒烟蔓草间。
秋海蔚陪笑道:“师姐,你到这西北蛮荒之地有事吗?师父她老人家可好?”
容潇湘哼了一声,“你以为,我在给谁穿孝?”
秋海蔚脸色一变,“难道师父……”
容潇湘冷冷地道:“师父二月十九去世了。”
“啊!”秋海蔚身子一晃,险些栽倒。
容潇湘续道:“师父的后事,我和师弟师妹们已经办了,本想召你回去的,但塞北江南千里迢迢,必然赶不及,也只得作罢。只是,师父临终还念念不忘李斜阳的事情,秋师弟,你听明白了吗?”
秋海蔚神色惨然,“我知道,师父遗命,让你来督促我取斜阳性命,是么?”
容潇湘道:“不错。师父知道你们感情不浅,她老人家在时,你尚且顾念私情,虽来到边塞斜阳堂,却与李斜阳避不见面,她老人家一死,没人从旁督促,就再过得三五十年,李斜阳也照样在斜阳堂活得好好的。”她瞥了一眼秋海蔚,又道:“秋师弟,不是我逼你,但你就这样拖下去,毕竟对大家都没什么好处。”
秋海蔚瞪着容潇湘,道:“师姐的意思是……”
容潇湘沉声道:“明天。”
秋海蔚全身一震,脸色刹时一片惨白,他张嘴刚想说什么,忽然容潇湘向草堆中厉声喝道:“什么人鬼鬼祟祟地躲在那里?给我出来!”随着话声,她一抖手向草丛中打出了一把铜钱。
草丛中两人飞身而起,身形急闪,那一把铜钱尽数打空。这两人在一丈外站定,秋海蔚一看,却原来正是酒楼上写侠史的“四哥”“九妹”。
“四哥”向容潇湘秋海蔚抱拳道:“胜夫人,秋大侠,在下与舍妹追随二位到此,并无他意,只想请胜夫人回答几个问题。”
容潇湘斜睨二人,冷冷地道:“我早已说过,先夫之事,恕我无可奉告,你们又何苦苦苦纠缠?”
“九妹”道:“胜夫人此言差矣,胜大侠之死颇多可疑,夫人难道对此无动于衷么?即使夫人不想弄明白此事,‘神谷’却不愿胜大侠死后留下不清不白之笔,还望夫人成全。”
容潇湘脸色一寒,“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四哥”道:“没什么意思,只是江湖传言对胜大侠和胜夫人都不大好听。”
容潇湘毫无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杀气,“你们好罗嗦!”
“九妹”昂然道:“我们只是欲求真相罢了。”
容潇湘厉声道:“没有真相!你们趁早给我滚,否则我可要动手赶人了。”
“四哥”怒道:“胜夫人,你好生无礼,我们好歹也是‘神谷’弟子,岂是任你呼喝的?”
容潇湘冷笑一声,“那又怎样?我还有更无礼的呢!”话音方落,她便纵身而起,双掌齐出,分向“四哥”“九妹”二人拍去。二人身形一闪,各向两旁退开,他们心知容潇湘乃秋水长天阁首徒,武功了得,实不欲与她动手硬拼,何况秋海蔚也在此处,此人武功,传说已傲视武林而无敌手,他们师姐弟联手,可要比自己兄妹强出太多,若衅从己开,只怕后果严重。
蓦然,“九妹”一声尖叫,“四哥”与秋海蔚一看之下,也各发出一声惊呼,原来“九妹”落下之处,竟是一块山边断岩,人落身其上,这石头吃不住劲,便向山下掉去,而人也随之落下。
“四哥”额上青筋迸跳,他反手自袖中拔出一柄精光闪烁的短刀,怒吼一声,便向容潇湘扑去。
容潇湘见到“九妹”坠崖,也暗吃一惊。她本意不过是逐走二人,不料而今成了这样的结果,也不由得她暗叫糟糕,为今之计,便只有杀人灭口,将这男子也杀了,否则与“神谷”结仇,绝非幸事。一念至此,她也不再客气,探手自腰间拔出一柄其薄如纸的软剑,迎风一抖,剑花朵朵,便向“四哥”袭去。
两人武功在伯仲之间,又都各存了杀人之念,出招俱都极尽狠辣之能事,斗得甚是凶险。秋海蔚在旁观战,既希望此事终能善了,又明知两人不分生死绝难停手,不由得好生踌躇。
正当容潇湘与“四哥”斗得激烈之时,忽然人影一闪,一道寒光在两人之间劈下,两人一凛,只得各自退开。
场中已多了个华服男子,此人手提长剑,嘴角微微含笑,扫了三人一眼,却并不说话。
三人谁也不知此人是谁,何时来到此地,因何而来。
“四哥”知今日绝难讨好,趁此机会,指着容潇湘道:“容潇湘,你等着,但教我等有三寸气在,必报九妹之仇。”言罢向那华服男子一抱拳,“兄台大德,金某日后定当报答,多谢。”随即下山而去。
容潇湘冷冷地打量着面前这男子,其人三十四五的年纪,一张脸十分中倒有七八分象是假的,虽也是浓眉大眼,却绝对谈不上“英俊”,嘴角虽带着两分笑意,整张脸倒透着八分诡异。她打量良久,总觉得此人似曾相识,但偏偏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这男子上上下下打量了容潇湘半晌之后,蓦然仰天大笑,笑声回荡在天地之间,也带着股说不出的诡异。就在长笑声中,这男子拔身而起,三晃两晃,便消失在了暮色苍茫之中。而容潇湘,仍兀自站在山上发愣。
树林里,篝火旁。
地上躺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双目紧闭,脸色雪白,但身上并无伤痕,正是“九妹”。
过了良久,她才终于缓缓苏醒过来,睁开眼,她第一眼看到的,是个男子高挑而颀长的背影,晚风吹过,衣袂飘飘,很是潇洒,但也相当陌生。她皱了皱眉,身子一动,却忍不住呻吟了一声,原来她一动才感到,自己全身酸痛难当,四肢百骸都象要散了似的。
那男子听得她呻吟之声,转身来到她身边,柔声道:“你醒了?很疼吧?不要紧,静养个十天半月就好了。这山虽然不高,摔下来的力道可也不小,可惜我接不住你。”他声音清悦温柔,“九妹”听了,心下不由好生感动,“相救之恩,小女子不知如何报答,不知恩人尊姓大名?”
那男子却只是笑笑,并不回答她的问题。“九妹”就着火光,终于看清了他的脸,大约三十四五的年纪,眉很浓很英挺,鼻子很大,脸给人的感觉是白惨惨的,只是他那双眼睛……那双眼睛……竟是好一双多情的眼!
那男子瞅了她几眼,忽然问:“姑娘贵姓?”
“九妹”想也没想,脱口便道:“我姓金。”回答完了,她才“哎呀”一声,道:“我不能说的。”
那男子没理她的话,又问:“芳名?”
“九妹”犹豫良久,最终却还是回答了他:“金叶。”
那男子笑道:“金叶?那是秋天的叶子,已经黄了,你正当青春年少,还不如叫‘柳叶’或是‘绿叶’呢。”
“九妹”抿嘴一笑,“姓是爹娘给的,名也是爹娘起的,我有什么办法?”
那男子道:“今天在山上那男的自称‘金某’,你也姓金,他是你哥哥?”
“九妹”道:“是,他是我四哥,他……”
“放心,他没事。”那男子沉吟了一下,“按理,我不该打听,可是你们怎么会跟容潇湘动上手的?”
金叶道:“也没什么,只不过我们一再向她打听胜箫的死,她就恼羞成怒,向我们出手了。”
那男子失笑道:“她谋杀亲夫,听你们问她,不犯急才怪。”
“什么?”金叶愕然,“你说她谋杀胜箫?”
“我随便说说的,别当真。”那男子扬了扬眉,“你们问胜箫的事做什么?他都死了那么多年了。”
金叶这回却只是歉声道:“对不起,这我真的不能说。”
那男子也不以为忤,转而道:“你的伤虽然不轻,走走路倒还勉强可以。天亮以后,你要去哪儿?我或许可以送你一程。”
金叶毫不犹豫,道:“去斜阳堂。”
“什么?”那男子一怔,“去斜阳堂?你去斜阳堂干什么?”
金叶微微一笑,“见胜传烽。”
那男子更为惊讶,“你们认识?”
金叶摇了摇头。
那男子问:“那你去干什么?胜传烽声名狼藉,象你这样的年轻女孩子,一说要见他,别人心里不知把你想得如何不堪。”
金叶道:“就算这样,我还是要见他。”
那男子道:“为什么?你非见他不可么?”
金叶道:“对不起,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原因。可是,我非要见他一面才行。”
那男子望着火堆,过了好一会儿,才道:“你要去斜阳堂倒很容易,这儿就是斜阳堂后园。不过,我劝你还是求见李斜阳吧。反正,你若说要见胜传烽,又不肯说出原由,中间不知有多少人会来盘问你,而最后见到的,却一定是李斜阳,倒不如你一开始就直接求见她,还省了诸多麻烦。”
金叶诧然道:“那如果李斜阳不在,别人岂不是就见不到胜传烽?”
那男子微笑道:“情形不同自当别论。很多尺度,不是斜阳堂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金叶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说:“我知道了,多谢你。”
那男子想了想,忽道:“你离开斜阳堂以后,能不能再回到这儿,把你的感觉告诉我?”
金叶道:“当然可以。可是,你听来有什么用?”
那男子一呆,笑着摇了摇头,“没什么用。”笑容苦涩,竟大有无可奈何之慨。
只是,这股神情,在他脸上稍纵即逝,他一转念间,忽又问道:“怎么,你不去和你哥哥会合?他要找容潇湘为你报仇呢!”
金叶叹道:“我何尝不想找他们?只是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现在会在哪里,却从何找起?反正,容潇湘和秋海蔚明天必定会去斜阳堂,他们要找容潇湘报仇的话,也必会在斜阳堂等她,到时,总能碰上的吧。”
那男子闻言一惊,“你说容潇湘和秋海蔚明天会去斜阳堂?他们去干什么?”
金叶道:“杀李斜阳,清理门户。”
“什么?!”那男子浑身一震,失声道,“李斜阳出身秋水长天阁?”
金叶“啊”了一声,“我说漏嘴了。”
那男子直直地盯着她:“你说的都是真的?”
金叶点了点头。
那男子狐疑地看着她,“你怎么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金叶微微一笑,“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不能告诉你。”
天光既亮,红日初升,林子里弥漫着一股早晨的清新之气,可那男子却对此毫未留意。
金叶已然走了,他一个人在篝火的余烬旁来回地踱着,眉峰深锁,显然心事重重,他一边踱着,一边还喃喃自语着什么。
金叶回来的时候,他正低头喃喃道:“怪道斜阳堂不问出身来历,堂主啊,原来你自己就是秋水长天阁的弃徒……嘿!这么说,我们倒是同病相怜了……”
金叶“咦”了一声,暗道:“这人究竟是谁?他在斜阳堂什么身份?斜阳堂里谁和李斜阳‘同病相怜’?”她这时才发觉自己竟依然不知这人的姓名来历。
那男子一抬头,见到金叶,眉峰一舒,笑道:“你回来了。见到胜传烽没有?”
金叶摇了摇头,“他不在,斜阳堂上下好像也都在找他。李斜阳说我可以留在那儿等,我记挂你还在这儿等我回音,而且李斜阳写了封信,让我见到你交给你,所以来了。”说话间,她拿出封信来递了给他。
那男子接了信并不就拆,却笑道:“李斜阳对你很不一般哪,你到底什么身份?”
金叶心不在焉地看着远处,对他说什么根本不曾听进去。
那男子对她这样子又是吃惊又是好笑,当下也不再和她说话,只留意看着她脸上的神情变化。
她凝眸沉思着什么,忽然叹息了一声,但随后却又展颜笑道:“见到李斜阳,我才知道了什么叫做‘冰河解冻’!。”
那男子不料等出的竟是她这样一句话,愕然问道:“你在说什么?”
她眼波流转,“我是说,以前别人形容有些人笑起来的样子象是冰河解冻,我以为那不过是夸大其辞的说法,可是见到了李斜阳,我才知道,原来一个人真的可以在不笑的时候那样冷若冰霜,而一旦笑起来,又立时使人觉得如沐春风般地温暖亲切。”
那男子不以为然地一笑,道:“你别小看李斜阳的笑,她的笑和她的剑一样,都是最可怕的武器。”
金叶扬起了眉,“哦?”
那男子道:“你不信?你知不知道斜阳堂何以能有今天的势力,李斜阳何以会有今天的地位?就是因为她的笑!她的笑,带着股孩子的纯真,可以让别人对她丝毫不加提防,可以让人低估了她的力量与手段,也可以让别人毫无怨言地替她卖命!”
金叶侧首看着他,“你究竟是谁?怎么对李斜阳这么清楚?”
他微微一笑,却没说什么,低下头专心看信,看完之后,抬头打量金叶许久,脸上神情甚是惊异。
金叶不由自主伸手在脸上摸了一把,问:“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脸上长花了么?”
他摇了摇头,道:“原来,你竟是神谷子弟。”
金叶万没想到李斜阳给他的信中,竟会说了自己的身份,一时心下极为狐疑,将这两人一言一行又细细捉摸了一遍,蓦然脑中灵光一闪,也不急推敲,已失声道:“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胜――传――烽!”
那人也想不到她这样就能猜出自己身份,张口结舌愣了好一会,才正容道:“不错,我就是胜传烽,你千方百计地找我,就为了你们的《胜传烽传》么?”
金叶道:“不错。我是‘神谷’弟子,此次同几位兄长出谷,目的就在于撰写《胜传烽传》。胜先生的出身来历江湖上各种传言,莫衷一是,‘神谷’作传秉的是史家春秋之笔,故不揣冒昧,想请胜先生明告。”
胜传烽道:“神谷是不是人太多没有事情做?《胜传烽传》?我还没死呢。”
金叶轻轻一笑,“不一定非要死人才能立传的。”
胜传烽想了想,又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写《李斜阳传》?我胜传烽所做的事无一不与堂主有关。”
金叶道:“这就是‘神谷’的事了,不劳费心。”
胜传烽沉吟良久,方道:“我考虑一下,不过,你都写了点什么得先让我看看。我的出身来历,也许可以直接写给你们,但是要你们回到神谷之后方可启看。”
金叶笑道:“那没问题,不过底稿在我七哥那,先要见到我七哥才行。”
胜传烽望着他,“你说他们会去斜阳堂等容潇湘?李斜阳知道这些事吗?”
金叶点了点头,“我和她说了。”
胜传烽追问道:“她对容潇湘他们……有什么表示?”
金叶道:“当时她皱了皱眉,说:‘这倒是天意如此了!我见他们,必拼个你死我活,若是我死,这时毫无准备,胜传烽不见得能统御诸人,斜阳堂将要大乱。关中之乱,我本来在为是自己去还是让胜传烽去烦恼,吴川之叛,我和传烽皆可平,只是方式不同……这样一看,倒还是我去吧。你见到胜传烽,不妨把这话转告他。再告诉他,我知道这样也是难为他,可是,我相信以他的武功智慧,当不致有失。’然后她写了那封信,就带着几个人行色匆匆地走了。”
胜传烽诧异道:“你知道吴川将叛?”
金叶点点头,“李斜阳是当着我面接到这个消息的。”顿了顿,她忽然想到什么,奇怪地看了一眼胜传烽,道:“咦,昨天晚上我一说容潇湘和秋海蔚要杀李斜阳清理门户,你怎么就知道她出身秋水长天阁了?一般江湖中人,不应该知道有这么个门派的。”
“这……”胜传烽一时竟为之语塞。
金叶又想了想,道:“奇怪,你听到容潇湘这事,应该马上回斜阳堂才对,可是你怎么连一点都不急?”
胜传烽冷笑一声,“我急什么?我虽未见过堂主出手,可我知道在秋水长天阁最得阁主真传的并不是秋海蔚,更不是容潇湘,而是三个大弟子中另一人。”
金叶倒抽一口冷气,“你对秋水长天阁这么清楚!你是不是真的就是胜箫?胜箫死于六年前,斜阳堂创立于五年前,胜传烽也出现于五年前,时间上可吻合得很。”
胜传烽一笑道:“我的来历是我考虑要不要告诉你的事,你那么急打听干什么?”
斜阳堂。
容潇湘站在斜阳堂前,看着面前雕梁画栋的建筑和大门前挂着的“斜阳堂”的匾额,忍不住叹了口气,向秋海蔚道:“如此古朴雄伟的建筑,一看就知道必出于李斜阳设计;如此飘逸苍劲的字迹,一看就知道必出于李斜阳手笔……我虽一向和李师妹不睦,可我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胸怀才具。”
秋海蔚站在斜阳堂前,看着面前出于李斜阳设计的建筑和出于李斜阳手笔的匾额,忍不住也叹了口气,他眼中本就带着一股浓重的无奈和悲痛,此时更平添一份黯然伤魂。
“容潇湘,你站住!”容潇湘和秋海蔚方要抬步,蓦听得有人断喝一声,随即三个男子闪身挡在两人身前,正是“神谷”那三个弟子。
“七哥”抱拳道:“胜夫人,秋大侠,昨天的事四哥已经和我们说了,这件事如何解决,我们想听听二位的意思。”
容潇湘木然道:“你们划下道来,我接着就是,何必假客气?”
“七哥”看了一眼秋海蔚,“我们的意思,这件事是我们金家的人和你胜夫人之间解决,还是神谷和秋水长天阁之间了断?”
容潇湘冷冷道:“你们既不念师门数代交谊,秋水长天阁也不见得就怕了神谷。”
秋海蔚听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忍不住插言道:“三位,昨日之事纯属意外,何必……”
“四哥”冷笑一声道:“秋大侠,我敬你素日侠义无双,可想不到你竟也说这种风凉话!”
秋海蔚道:“这怎么是风凉话?昨天的事,你们这里也不是没人在场,那不是意外是什么?虽说各位有丧妹之痛,却也不能定说是我师姐害死令妹的。”
“三哥”道:“老七,和他们多说什么,我就不信我们还怕了他们!”
“七哥”皱眉道:“这么说,秋大侠是不肯置身事外了?”
秋海蔚看看容潇湘,她脸上仍是漠无表情,他长叹一声,道:“师姐有事,师弟自当服其劳。”
“七哥”道:“好!二位请,九妹在何处遇难的,我们就在哪里了断。”
容潇湘冷哼一声,转身刚要走,忽听斜阳堂内有个女子高声叫道:“等一等!”
金氏兄弟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正匆匆跑下台阶,向他们奔来,正是金叶。
三人又惊又喜,忙迎上前去,少不得一番问长问短。
金叶向斜阳堂门前一指,道:“是他救了我。”
斜阳堂大门之前,牌匾之下,有个男子正负手而立,脸上带着股似笑非笑的神情,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却仿佛与他们隔得极远极远,完全是在两个世界中似的。
“七哥”抱拳道:“多谢相救舍妹,不敢请教先生尊姓大名?”
那人微微一笑,拱了拱手,“在下胜传烽。”
秋海蔚听得“胜传烽”三字,心猛然间一紧,霍然抬头,他看着胜传烽,怎么也难以相信,这男子竟就是自己听说了多少次的胜传烽——
“李斜阳竟然选中这么丑的男子?”
“胜传烽居然如此潇洒?”
“他究竟是不是未死的胜箫?”
“李斜阳到底是否真和他不清不白?”
“李斜阳是和他逢场作戏呢还是真的喜欢他?”
“……”
秋海蔚看着胜传烽,心中各种念头纷至沓来,一时呆了。
金氏兄弟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费尽心血打探的胜传烽竟会这样被他们碰上,一时竟也说不出话来。
胜传烽扫了一眼门前这些人,忍不住笑道:“你们怎么都不说话?”
容潇湘脸色难看至极,她嘎声问:“你姓胜?”
胜传烽点头道:“不错。容女侠有何见教么?”
容潇湘道:“你和胜箫有什么关系?”
胜传烽道:“他姓胜,我也姓胜,如此而已。”
容潇湘追问道:“没别的关系了么?”
胜传烽脸色一冷,“当然。”
容潇湘却咬着牙一字字道:“我——不——信!”顿了顿,她道:“昨天我就看你眼熟,只是想不起来你象谁。你和胜箫都姓胜,长得也很象,连声音都差不多,你敢说你们没别的关系?”
胜传烽嘴角一斜,“信不信由你,我没功夫和你争论这些。各位在斜阳堂门前,有事要找斜阳堂么?没事就请便吧。”
“七哥”看一眼金叶,金叶低声向他说了些什么,他颇感意外地抬头看了一眼胜传烽,便取出一叠稿子交给金叶,一边道:“我昨晚修改了一些,又重新誊了一遍,胜先生肯指教,那是最好。”
金叶将这叠稿子捧到胜传烽面前,胜传烽接了交给身后一人道:“送到我屋里去,小心点,别弄乱了。”那人应了,退下。
容潇湘道:“我们要见你们堂主。”
胜传烽道:“对不起,堂主不在。”
容潇湘脸色一寒,“胜传烽,你也是江湖上有名有姓的人物,怎么当面撒谎?”
胜传烽沉着脸道:“我如何当面撒谎了?堂主在不在,是你知道还是我知道?”
容潇湘眉一沉,道:“就算她不在,我们也要在斜阳堂等她,等到她在为止!”
胜传烽斜眼瞅着她,“你们在斜阳堂等?凭什么?”
“我是她师姐,秋海蔚是她师兄。”
“对不起,我不知道堂主有没有你们这两位师兄师姐,恕我不敢招待。”
容潇湘怒道:“胜传烽,你简直是在耍无赖!”
胜传烽冷冷一笑,“我这是维护斜阳堂。否则,任什么人空口白话说一句自己是谁的师兄师姐就能进斜阳堂,斜阳堂早就被洗劫一空了。”
“什么?”容潇湘益怒,“你竟指我们为强盗?”
“我可没这个意思。不过既然容女侠已自承为强盗,斜阳堂就更不敢招待了。”
容潇湘瞪着他,眼睛里如要冒出火来,胜传烽却只是嘴角挂着个冷诮的笑,斜眼瞅着她。
“胜先生——”就在两人僵持之际,“七哥”忽地插言道,“我们可以证明,他们二位,确实是李堂主的师兄师姐。”
胜传烽的笑容更为冷诮,他打了个哈哈,道:“既然‘神谷’高足肯作证,我可倒不好意思再难为二位了。如此,几位都请到大厅奉茶。”
胜传烽将五人让入大厅,分别落座之后,“七哥”向胜传烽道:“胜先生,‘神谷’交稿之期为夏至之日……”
胜传烽一笑,“我知道……这样吧,今晚我来拜访金七先生如何?”
“七哥”点了点头道:“那就烦劳胜先生了。我们住在斜阳堂对面的云来客栈里,今晚恭候胜先生大驾。另外——”他看了金叶一眼,道:“我等有一不情之请,不知胜先生肯不肯俯允。”
胜传烽道:“是不是金姑娘有伤在身,不宜旅途劳顿,七先生想让她在斜阳堂住一段日子?”
“七哥”一愣,道:“不错。”
胜传烽笑道:“平日里,就想请‘神谷’高足来作客,亦不可得,而今难得可以为金姑娘效劳,我等真是求之不得,又怎么会不肯?……金姑娘在此,也正好可以看看堂主和秋大侠之战,不妨多住两日。”
“七哥”听了胜传烽最后那句话,脸上不由一红,他心里,正是想让金叶留在此地一睹李斜阳与秋海蔚的决战的,却不料胜传烽一语便道破了他的用意。他坐在那里,讪讪地有些不是滋味,便与“四哥”“五哥”借故告辞了。
月明中天,夜深人不寐。
金叶知道胜传烽曾在他们的底稿上作了些加注修改,可是他究竟写了些什么,她也并不知情。
她看着三位兄长相携离去,听着马蹄声踏着西北的风沙渐行渐远,心里,不由得一阵凄惶,觉得自己,孤独无助起来。
这时,胜传烽在她身旁柔声道:“金姑娘,回去吧。令兄他们,很快就会回来接你,你安心在斜阳堂住着,若缺什么,也尽管说。如果觉得孤单,斜阳堂中也有不少女子,我可以找人来陪伴姑娘……”
金叶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却又立时低下头去,想起自己所写《胜传烽传》中的一段:“人以其城府甚深,号之曰‘青蛇’。蛇者,阴毒之物也,人恒厌之。传烽处世,虽圆通明理而终乏诚恳之意,故友之长远者,唯二三人耳。传烽尝助峨嵋报黄夕、秦可之仇,初时诸女感激,然后方知其所为者,秦可所遗拳剑也,终鄙弃之。传烽尝与方骏善,骏有难,传烽助之,然多怨言,骏虽不怿而不能言,后骏私一女,传烽见之,悦其色,戏之,骏无可忍,终与断义……”她心里一阵惊竦,却隐隐约约地,开始怀疑起那些“三哥”“四哥”亲自调查取证的事的真实性来。
两人缓缓走向斜阳堂,却发觉,不知何时,斜阳堂门前,竟站了一个瘦削伶仃的人。
胜传烽仔细打量了他两眼,才迟疑地道:“是……秋大侠?”
那人“嗯”了一声,“我是秋海蔚。”
胜传烽眼中泛起一抹惊警之色,“那么晚了,秋大侠还不睡么?”
秋海蔚沉默许久,终于长叹一声,道:“你知道,李斜阳是我什么人吗?”
胜传烽与金叶俱自一愣,对视一眼,金叶道:“你们不是要清理门户么?难道,难道……她不是原名李青竹后改名李斜阳的秋水长天阁第三弟子?”
秋海蔚干笑一声,“原来,‘神谷’对秋水长天阁的事,的确不了解。不错,她是我三师妹,可是……”
他顿了顿,直视着胜传烽,接道:“她也是我的妻子。十年之前,我已曾为她与胜箫一战。”
胜传烽倒抽了一口冷气,脸色愈发显得惨白,可他双眼中却闪起了一道炽芒。他笑了笑,说:“这么说,秋大侠今晚,是想与胜某决一胜负,甚至,定出生死了?”
秋海蔚迟疑了一下,却说:“我……不知道。”他有些失神的眼光瞥着胜传烽,踌躇良久,终于悄然问:“你和她,真的……?”
胜传烽肯定地点了点头。
秋海蔚默然不语。
却听一阵笑声自长街另一头传来,随即响起一个男子沙哑的声音,“真是天公不知人间事。今夜不应明月当空,想此情此景,若是狂风大作,响几声霹雳,才不负长街对决之慨。”
三人一齐转头,却见长街外,一个形容落拓的汉子,一手执着酒葫芦,一手提一条长鞭,边喝边行,脸上已有三分醉色。
他也不看三人,又兀自道:“想当年,姑苏一战,秋海蔚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胜箫又是何等的豪情胜概,虽是暴雨滂沱,天下英雄今日思之,也振奋不已。想不到十年之后……嘿嘿……”
他毫不理会三人的目光,穿过长街,便消失在了黑暗中。
胜传烽望着他背影消失之处,喃喃道:“又是他!”
金叶先是一阵惊异,其后却恍然大悟,她曾写过这个人:“其人(胜传烽)性风流,裙钗中常有薄幸名。七年,出洛阳,拐张氏妇,燕好七日,发金归之。妇羞恚交秉,自缢于慈云庵。其夫洛阳武师王易庭,欲制传烽死命不得,迁居斜阳堂前,每有风吹草动,辄行挑唆,必使传烽应战尔罢。传烽怒,欲杀,而斜阳不许。”
这个汉子,大约便是那洛阳武师王易庭了。
秋海蔚望着他背影消失之处,却渐渐握紧了双拳。他蓦然回头,向胜传烽道:“胜先生,按理,我不该在主人未归时便生事端,只是,你我之间的事,若等斜阳回来,只怕更难了结……”
胜传烽冷冷一笑,打断他的话道:“不错,无论是我和堂主有染,还是因为秋大侠要杀堂主,我们这一场,是迟早要决的。那么,秋大侠,请。”
秋海蔚苦笑着点了点头,“好,胜先生,请。”
金叶悄悄退开几步,她能感觉到,这街上的气氛已全然变了,空气在瞬间绷紧得仿佛天地都已是死的一般。
山雨欲来风满楼。
剑风乍起。
胜传烽终于出手。
秋海蔚心头一震——这剑气,他很熟悉——在他成名之战中,他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剑气!
十年以来,他无时或忘。
虽然胜传烽的招式奇特而诡异,为他生平仅见,可那剑气,却正是他十年来思之依然不安的——胜箫的剑气!
金叶在“神谷”,是读过十年前姑苏城外那一战的记载的。
那时的胜箫,已是名满天下的青年剑客,“白马啸啸,素剑朗朗,醉倚红楼,起振云霄”,不知羡煞了多少豪杰,倾倒了多少红妆。
而当时的秋海蔚,则尚籍籍无名于江湖,但“姿容澹然而不改其神飞风越,寒衣简服而不掩其意夺天地”,气势骎骎然,叫人意为之折。
故此,那一战,又被誉为“秋意胜概”。
两人之战,“飞虹四坠,霹雳两分,千古豪杰为之气咽,天下英雄为之色变。幽冥为之噤声,天光为之凝滞,彼野萧萧,彼心凄凄,不尽急雨,玉碎瓦全。”
这一战,两人都受了不轻的伤,但直至血染征衣,也还是平分秋色。
这一战之后,秋海蔚声名鹊起,胜箫更由此列身天下七大名剑。
这一战,人们至今犹为传颂。
秋海蔚胜传烽交手三招。
三招中,胜传烽的剑气虽然冷削,秋海蔚却始终不曾拔剑。
胜传烽却仍毫不留情,一剑快似一剑,一剑狠似一剑,每一剑,秋海蔚都是在间不容发间避了开去的。
终于,秋海蔚手中清啸声起,一道眩目的光华闪过,胜传烽手中长剑铮然而断。秋海蔚手中的剑进而点在胜传烽咽喉之上。
两人四目交投,谁也不出声,胜传烽眼中,隐隐流露出一股不甘不服之色。
与此同时,金叶失声惊呼:“秋情玉魄剑!”
秋海蔚手中握的,是一柄长约一尺七分,通体晶莹剔透的玉剑,剑虽光华润泽而明艳,却依然让人觉得怆然无比。
秋海蔚凝视着胜传烽,心中不知转过了几千几百个念头,终于还是长叹一声,缓缓收剑入鞘。
胜传烽看着他,淡然道:“这只是你的剑不平常,并不是你胜过了我。”他向金叶招了招手,“金姑娘,我送你回房。”
金叶看了一眼秋海蔚,轻声道:“秋大侠,我先走了。”低下头,随胜箫而去。
两人正要跨进斜阳堂大门时,胜传烽忽又停步,回头向秋海蔚道:“秋大侠,你进门的时候,烦劳关一下门,多谢了。”
秋海蔚木然站在街心,不知过了多久,耳边响起一个冷冰冰的女子声音:“你为什么不杀他?”
秋海蔚缓缓转身,看着容潇湘,“因为,他是胜箫。”
容潇湘迎着他的目光,冷然道:“那你就更该杀了他。”
秋海蔚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点什么,也不想逼师姐说给我听……对我来说,十年前,与胜箫一战之后,胜过胜箫,便成了我最大的心愿……我并非不想杀她,可是,我也希望,能公平决战。”
他顿了顿,又道:“何况,这毕竟是斜阳一手创办的基业,如今她不在堂中,我若杀了胜传烽,形势立将大乱……”
容潇湘冷笑一声,“不错,你若杀了她的姘头,可怎么向她交代!她会恨你一辈子,再也不回你身旁……”
秋海蔚脸色刹时铁青。
容潇湘却不理他,冷冷一笑,回身向斜阳堂走去,边走边道:“你不肯杀他,我自己也一样可以杀他,希望,他有命等到你们公平决战那一天吧!”
第一章完(1997年起稿,2002年完稿)
作者:蓝缕
所有的叶子里,枫叶是最美丽的。
他只是自顾自地深情地红着,却不知有人在为他颠狂。那是柳絮,一个夏日的颠狂者,却在秋日的萧瑟里,随风而去。
红是红地热烈,即便辗转秋风里,兀自溢着生气,而纤细的柳枝,只能在昏昏然的天气里,摆动她的腰肢,她想告诉别人什么呢?
柳儿千百度地兴叹,她渴求能见上红叶一面,可,他们实在是无法并世而存的。
红叶舞秋山,偌大一个山谷里,漫山遍野的就只是红叶,他沉溺在自己的美丽里。他不知道就在不久之前,在那河泽之畔,有人为他寸寸而折。他不曾要求什么,他一生都只呆在这山谷里,呆在自己的世界、一个只有他的世界里。他总认为,这里,便是世上最可爱的所在了。除了这空旷的山谷,除了他自己,他的眼里,便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
红叶哟,那动人的风姿、那片片的深情、还有那倘着孤傲的血液的脉络,在风起时,低诉着秋的景致。这一生,他的所闻所见,只有这秋,而他的心里,也是只有这瑟瑟之秋。
没有人明白他,人们见到的,总是那生气盎然而又浓烈如火的他,有谁知道,在他的脉络里流淌着的,除了那份孤傲,更有一份深深的寂寞。孤是与生惧来的,而这寂寞,却是他所甘愿。
没有人知道,连柳儿都不曾知道。这对于她,是一种悲哀,而对于他,则更是一种侵浸入髓的悲哀。
柳儿企图让时光快些过去,好在那秋日,见他一面。时光是逝去了,经霜的红叶,愈加艳地动人,而她自己,却已无存;时光又逝去了,等她再来时,红叶又无存。
纵生生世世,都奈何是无缘。
红叶随风舞,风中,仿佛有他低诉的声音;柳絮寸寸折,河畔,仿佛有她醉意的叹息……
——一九九七.十.十一.
久久的寂寞啊,或许已经习惯了。那深情的红叶,终究是有柳絮遥遥地伴着他。
颠狂柳絮随风去,深情红叶逐水流。但愿,柳絮入泥,红叶坠地,好相聚在尘俗里……
——蓝缕
————————————————————————————————————————
斜阳劫
序
引《情叶》于《斜阳劫》之前,并不是两者有什么关系。《情叶》是《情叶》,《斜阳劫》是《斜阳劫》,二者毫无关联可言。
“但愿,柳絮入泥,红叶坠地,好相聚在尘俗里……”这句话,是我将《情叶》引于《斜阳劫》之前的最直接的原因。有种感觉,《斜阳劫》仿佛就是柳絮与红叶在尘俗里的相聚的传奇。然而,《斜阳劫》里其实是没有人可与那般凄艳的柳絮与红叶比拟的。
将《情叶》引于《斜阳劫》前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斜阳劫》是为某个人而写的。
《斜阳劫》构思于三年前,但一直以来都只有个隐约的框架,连主要人物,也仅有一个名字。如果不是认识了这个人,或许再过三年,它也依然苍白如初。
这个人,可以认为便是使柳絮寸寸而折的红叶。
“颠狂柳絮随风去,深情红叶逐水流。”
但,那遥遥地伴着红叶的柳絮,不是我。
九八.一.九
请鸿轩
第一章
日暮,斜阳千里,彤云如火。
秋海蔚在斜阳里,“斜阳阁”的斜阳里。
与其说他喜欢斜阳,不如说他对一切带着“斜阳”这两个字的事物,都有种特殊的亲近之心。比如他来这家掌柜稀里糊涂,伙计没精打采,厨师马马乎乎的“斜阳阁”酒楼,就纯粹为了那个名字。
他喜欢“斜阳”这两个字,因为,有一个女子,名叫李斜阳,李斜阳手中有一股力量,是为斜阳堂。
“斜阳阁”的生意素来清淡,来这儿的人通常都不是为了吃饭。秋海蔚是为了它的名字,靠窗的一桌客人则十有八九是图它的清静。秋海蔚来的时候,他们便已经在那里了,四个人,三男一女,桌上放着纸、墨、笔、砚一应文房用具,那女子执笔,一男子磨墨,一男子捧纸,一男子替她翻查着什麽,四个人神情都很凝重,桌角上的几盆菜,始终没有动过。
那女子落笔极快,秋海蔚进来没多久,就看她换了有十几张纸,纸上写什么虽看不清楚,却可以大致看出满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
终于,她长吁了口气,放下笔,向那磨墨的男子道:“《胜传烽传》的底稿我起好了,七哥,接下来就看你的了。离夏至还有三天,给你润色修改总够了吧?”
那男子也吁了口气,展颜笑道:“就算明天是夏至也没关系,九妹的文字,还用得着我来改吗?”
“九妹”摇了摇头,“七哥取笑了。……只是,这篇传文语焉不详的地方太多,我看我们还是再参详一下的好。”
“七哥”沉吟了一下,拿过那篇文章,小声读了起来:“胜传烽,不知何许人也,有问之者,含糊以塞。或曰,胜传烽者,武当故剑客胜箫也。然询其何故别武当而入斜阳,则瞠目不知所对。探乎武当众侠,闻胜箫之名,立缄口,偶于江湖邂逅,辄侧目过,传烽亦冷笑不语。”
他住了口,想了想,“你在学《五柳先生传》么?胜传烽的来历,就这样算交代了?”
那翻查的男子接口道:“没办法,胜传烽的来历我和三哥怎么查也查不出来,连李斜阳都说不知道。”
捧纸的男子补道:“我曾经偷入过武当去查胜箫的资料,可是武当有关胜箫的一切记录都被销毁了。”
“七哥”挑了挑眉,“你们有没有去问过胜传烽本人?”
三人互相看看,同时摇了摇头。
“七哥”正色道:“‘神谷’写侠史,求的是秉笔直书,以往为已故者作传,引用传说,那是没办法,但胜传烽不是死人,他既然活着,不管他肯不肯说,你们都该去问问。这点道理,九妹刚开始编修武林史不知道,难道三哥四哥你们也不知道么?”
“三哥”“四哥”对视一眼,垂下了头,“九妹”则很爽快地道:“那,我明天就去斜阳堂见胜传烽。”
“七哥”点了点头,又接着念下去:“其于斜阳堂,位仅李斜阳之下,李倚重之,事无巨细,俱与商,达旦不以为异,并肩出入不以为怪,时遭非议。久之,人习为常,遂息。”
“四哥”冷笑一声,“九妹写得也太客气了,李斜阳和胜传烽私通,谁不知道?他们自己都不瞒着别人,你又何苦为他们遮遮掩掩的?”
从他们提到胜传烽这个名字起,秋海蔚就一直留神在听他们的对话,胜传烽和李斜阳的传言,他当然也听说过。现在,听到连“神谷”的人都这么说,他心里不由一阵绞痛,别人可能会胡说,可是,“神谷”的人,却绝不会胡说。
胜传烽,胜传烽是何许人也,秋海蔚心中暗下决心,他定要见识见识。
正在此时,“斜阳阁”又来了一个人,一个三十上下的少妇。
这少妇一身缟素,鬓边一朵白花,脸上冷冰冰的毫无表情,进门就朝秋海蔚而来。
秋海蔚见到她,脸色刹时变得很难看。
她在他桌前站定,先冷冷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又扫了眼四周,方道:“你眼里若还有我,就随我来。”她的声音也平平板板的,不带一丝感情。
秋海蔚缓缓站起身,缓缓道:“小弟敢不从命。”
少妇二话不说,转身向外走去。
他们走了,“三哥”忽然道:“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
闻言,“四哥”会心地一笑,“七哥”漠不关心地继续翻看着《胜传烽传》的底稿,“九妹”则饶有兴趣地问:“是谁?”
“三哥”得意地笑道:“那男的就是秋海蔚……”
“九妹”一惊,“秋情不绝系斜阳,无奈潇湘向胜郎?”
“三哥”愕然反问:“你在说什么?”
“九妹”道:“怎么,你不知道?这是舒家三姐的《秋水长天阁序》里的呀!秋水长天阁三个大弟子,再加上武当胜箫,所有的纠葛都在这两句诗里,是全文的点睛之笔,你难道没看过吗?”
“三哥”尴尬地笑笑,“我对舒家姑娘写的诗文不感兴趣……”
“四哥”“嗤”地笑了一声,道:“你对人家的诗文不感兴趣,那人家的人呢?”
“三哥”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你……”
“九妹”忙道:“你们别吵!三哥,那男的是秋海蔚,那女的又是谁?”
“三哥”道:“那女的?你不知道?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九妹”眼珠一转,“啊,她就是秋水长天阁的大弟子,秋海蔚和李斜阳的师姐容潇湘?”
“四哥”颔首道:“不错,她就是胜箫的妻子。我和三哥还特地找过她……这女人好凶!”
城外山冈上,荒烟蔓草间。
秋海蔚陪笑道:“师姐,你到这西北蛮荒之地有事吗?师父她老人家可好?”
容潇湘哼了一声,“你以为,我在给谁穿孝?”
秋海蔚脸色一变,“难道师父……”
容潇湘冷冷地道:“师父二月十九去世了。”
“啊!”秋海蔚身子一晃,险些栽倒。
容潇湘续道:“师父的后事,我和师弟师妹们已经办了,本想召你回去的,但塞北江南千里迢迢,必然赶不及,也只得作罢。只是,师父临终还念念不忘李斜阳的事情,秋师弟,你听明白了吗?”
秋海蔚神色惨然,“我知道,师父遗命,让你来督促我取斜阳性命,是么?”
容潇湘道:“不错。师父知道你们感情不浅,她老人家在时,你尚且顾念私情,虽来到边塞斜阳堂,却与李斜阳避不见面,她老人家一死,没人从旁督促,就再过得三五十年,李斜阳也照样在斜阳堂活得好好的。”她瞥了一眼秋海蔚,又道:“秋师弟,不是我逼你,但你就这样拖下去,毕竟对大家都没什么好处。”
秋海蔚瞪着容潇湘,道:“师姐的意思是……”
容潇湘沉声道:“明天。”
秋海蔚全身一震,脸色刹时一片惨白,他张嘴刚想说什么,忽然容潇湘向草堆中厉声喝道:“什么人鬼鬼祟祟地躲在那里?给我出来!”随着话声,她一抖手向草丛中打出了一把铜钱。
草丛中两人飞身而起,身形急闪,那一把铜钱尽数打空。这两人在一丈外站定,秋海蔚一看,却原来正是酒楼上写侠史的“四哥”“九妹”。
“四哥”向容潇湘秋海蔚抱拳道:“胜夫人,秋大侠,在下与舍妹追随二位到此,并无他意,只想请胜夫人回答几个问题。”
容潇湘斜睨二人,冷冷地道:“我早已说过,先夫之事,恕我无可奉告,你们又何苦苦苦纠缠?”
“九妹”道:“胜夫人此言差矣,胜大侠之死颇多可疑,夫人难道对此无动于衷么?即使夫人不想弄明白此事,‘神谷’却不愿胜大侠死后留下不清不白之笔,还望夫人成全。”
容潇湘脸色一寒,“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四哥”道:“没什么意思,只是江湖传言对胜大侠和胜夫人都不大好听。”
容潇湘毫无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杀气,“你们好罗嗦!”
“九妹”昂然道:“我们只是欲求真相罢了。”
容潇湘厉声道:“没有真相!你们趁早给我滚,否则我可要动手赶人了。”
“四哥”怒道:“胜夫人,你好生无礼,我们好歹也是‘神谷’弟子,岂是任你呼喝的?”
容潇湘冷笑一声,“那又怎样?我还有更无礼的呢!”话音方落,她便纵身而起,双掌齐出,分向“四哥”“九妹”二人拍去。二人身形一闪,各向两旁退开,他们心知容潇湘乃秋水长天阁首徒,武功了得,实不欲与她动手硬拼,何况秋海蔚也在此处,此人武功,传说已傲视武林而无敌手,他们师姐弟联手,可要比自己兄妹强出太多,若衅从己开,只怕后果严重。
蓦然,“九妹”一声尖叫,“四哥”与秋海蔚一看之下,也各发出一声惊呼,原来“九妹”落下之处,竟是一块山边断岩,人落身其上,这石头吃不住劲,便向山下掉去,而人也随之落下。
“四哥”额上青筋迸跳,他反手自袖中拔出一柄精光闪烁的短刀,怒吼一声,便向容潇湘扑去。
容潇湘见到“九妹”坠崖,也暗吃一惊。她本意不过是逐走二人,不料而今成了这样的结果,也不由得她暗叫糟糕,为今之计,便只有杀人灭口,将这男子也杀了,否则与“神谷”结仇,绝非幸事。一念至此,她也不再客气,探手自腰间拔出一柄其薄如纸的软剑,迎风一抖,剑花朵朵,便向“四哥”袭去。
两人武功在伯仲之间,又都各存了杀人之念,出招俱都极尽狠辣之能事,斗得甚是凶险。秋海蔚在旁观战,既希望此事终能善了,又明知两人不分生死绝难停手,不由得好生踌躇。
正当容潇湘与“四哥”斗得激烈之时,忽然人影一闪,一道寒光在两人之间劈下,两人一凛,只得各自退开。
场中已多了个华服男子,此人手提长剑,嘴角微微含笑,扫了三人一眼,却并不说话。
三人谁也不知此人是谁,何时来到此地,因何而来。
“四哥”知今日绝难讨好,趁此机会,指着容潇湘道:“容潇湘,你等着,但教我等有三寸气在,必报九妹之仇。”言罢向那华服男子一抱拳,“兄台大德,金某日后定当报答,多谢。”随即下山而去。
容潇湘冷冷地打量着面前这男子,其人三十四五的年纪,一张脸十分中倒有七八分象是假的,虽也是浓眉大眼,却绝对谈不上“英俊”,嘴角虽带着两分笑意,整张脸倒透着八分诡异。她打量良久,总觉得此人似曾相识,但偏偏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这男子上上下下打量了容潇湘半晌之后,蓦然仰天大笑,笑声回荡在天地之间,也带着股说不出的诡异。就在长笑声中,这男子拔身而起,三晃两晃,便消失在了暮色苍茫之中。而容潇湘,仍兀自站在山上发愣。
树林里,篝火旁。
地上躺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双目紧闭,脸色雪白,但身上并无伤痕,正是“九妹”。
过了良久,她才终于缓缓苏醒过来,睁开眼,她第一眼看到的,是个男子高挑而颀长的背影,晚风吹过,衣袂飘飘,很是潇洒,但也相当陌生。她皱了皱眉,身子一动,却忍不住呻吟了一声,原来她一动才感到,自己全身酸痛难当,四肢百骸都象要散了似的。
那男子听得她呻吟之声,转身来到她身边,柔声道:“你醒了?很疼吧?不要紧,静养个十天半月就好了。这山虽然不高,摔下来的力道可也不小,可惜我接不住你。”他声音清悦温柔,“九妹”听了,心下不由好生感动,“相救之恩,小女子不知如何报答,不知恩人尊姓大名?”
那男子却只是笑笑,并不回答她的问题。“九妹”就着火光,终于看清了他的脸,大约三十四五的年纪,眉很浓很英挺,鼻子很大,脸给人的感觉是白惨惨的,只是他那双眼睛……那双眼睛……竟是好一双多情的眼!
那男子瞅了她几眼,忽然问:“姑娘贵姓?”
“九妹”想也没想,脱口便道:“我姓金。”回答完了,她才“哎呀”一声,道:“我不能说的。”
那男子没理她的话,又问:“芳名?”
“九妹”犹豫良久,最终却还是回答了他:“金叶。”
那男子笑道:“金叶?那是秋天的叶子,已经黄了,你正当青春年少,还不如叫‘柳叶’或是‘绿叶’呢。”
“九妹”抿嘴一笑,“姓是爹娘给的,名也是爹娘起的,我有什么办法?”
那男子道:“今天在山上那男的自称‘金某’,你也姓金,他是你哥哥?”
“九妹”道:“是,他是我四哥,他……”
“放心,他没事。”那男子沉吟了一下,“按理,我不该打听,可是你们怎么会跟容潇湘动上手的?”
金叶道:“也没什么,只不过我们一再向她打听胜箫的死,她就恼羞成怒,向我们出手了。”
那男子失笑道:“她谋杀亲夫,听你们问她,不犯急才怪。”
“什么?”金叶愕然,“你说她谋杀胜箫?”
“我随便说说的,别当真。”那男子扬了扬眉,“你们问胜箫的事做什么?他都死了那么多年了。”
金叶这回却只是歉声道:“对不起,这我真的不能说。”
那男子也不以为忤,转而道:“你的伤虽然不轻,走走路倒还勉强可以。天亮以后,你要去哪儿?我或许可以送你一程。”
金叶毫不犹豫,道:“去斜阳堂。”
“什么?”那男子一怔,“去斜阳堂?你去斜阳堂干什么?”
金叶微微一笑,“见胜传烽。”
那男子更为惊讶,“你们认识?”
金叶摇了摇头。
那男子问:“那你去干什么?胜传烽声名狼藉,象你这样的年轻女孩子,一说要见他,别人心里不知把你想得如何不堪。”
金叶道:“就算这样,我还是要见他。”
那男子道:“为什么?你非见他不可么?”
金叶道:“对不起,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原因。可是,我非要见他一面才行。”
那男子望着火堆,过了好一会儿,才道:“你要去斜阳堂倒很容易,这儿就是斜阳堂后园。不过,我劝你还是求见李斜阳吧。反正,你若说要见胜传烽,又不肯说出原由,中间不知有多少人会来盘问你,而最后见到的,却一定是李斜阳,倒不如你一开始就直接求见她,还省了诸多麻烦。”
金叶诧然道:“那如果李斜阳不在,别人岂不是就见不到胜传烽?”
那男子微笑道:“情形不同自当别论。很多尺度,不是斜阳堂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金叶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说:“我知道了,多谢你。”
那男子想了想,忽道:“你离开斜阳堂以后,能不能再回到这儿,把你的感觉告诉我?”
金叶道:“当然可以。可是,你听来有什么用?”
那男子一呆,笑着摇了摇头,“没什么用。”笑容苦涩,竟大有无可奈何之慨。
只是,这股神情,在他脸上稍纵即逝,他一转念间,忽又问道:“怎么,你不去和你哥哥会合?他要找容潇湘为你报仇呢!”
金叶叹道:“我何尝不想找他们?只是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现在会在哪里,却从何找起?反正,容潇湘和秋海蔚明天必定会去斜阳堂,他们要找容潇湘报仇的话,也必会在斜阳堂等她,到时,总能碰上的吧。”
那男子闻言一惊,“你说容潇湘和秋海蔚明天会去斜阳堂?他们去干什么?”
金叶道:“杀李斜阳,清理门户。”
“什么?!”那男子浑身一震,失声道,“李斜阳出身秋水长天阁?”
金叶“啊”了一声,“我说漏嘴了。”
那男子直直地盯着她:“你说的都是真的?”
金叶点了点头。
那男子狐疑地看着她,“你怎么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金叶微微一笑,“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不能告诉你。”
天光既亮,红日初升,林子里弥漫着一股早晨的清新之气,可那男子却对此毫未留意。
金叶已然走了,他一个人在篝火的余烬旁来回地踱着,眉峰深锁,显然心事重重,他一边踱着,一边还喃喃自语着什么。
金叶回来的时候,他正低头喃喃道:“怪道斜阳堂不问出身来历,堂主啊,原来你自己就是秋水长天阁的弃徒……嘿!这么说,我们倒是同病相怜了……”
金叶“咦”了一声,暗道:“这人究竟是谁?他在斜阳堂什么身份?斜阳堂里谁和李斜阳‘同病相怜’?”她这时才发觉自己竟依然不知这人的姓名来历。
那男子一抬头,见到金叶,眉峰一舒,笑道:“你回来了。见到胜传烽没有?”
金叶摇了摇头,“他不在,斜阳堂上下好像也都在找他。李斜阳说我可以留在那儿等,我记挂你还在这儿等我回音,而且李斜阳写了封信,让我见到你交给你,所以来了。”说话间,她拿出封信来递了给他。
那男子接了信并不就拆,却笑道:“李斜阳对你很不一般哪,你到底什么身份?”
金叶心不在焉地看着远处,对他说什么根本不曾听进去。
那男子对她这样子又是吃惊又是好笑,当下也不再和她说话,只留意看着她脸上的神情变化。
她凝眸沉思着什么,忽然叹息了一声,但随后却又展颜笑道:“见到李斜阳,我才知道了什么叫做‘冰河解冻’!。”
那男子不料等出的竟是她这样一句话,愕然问道:“你在说什么?”
她眼波流转,“我是说,以前别人形容有些人笑起来的样子象是冰河解冻,我以为那不过是夸大其辞的说法,可是见到了李斜阳,我才知道,原来一个人真的可以在不笑的时候那样冷若冰霜,而一旦笑起来,又立时使人觉得如沐春风般地温暖亲切。”
那男子不以为然地一笑,道:“你别小看李斜阳的笑,她的笑和她的剑一样,都是最可怕的武器。”
金叶扬起了眉,“哦?”
那男子道:“你不信?你知不知道斜阳堂何以能有今天的势力,李斜阳何以会有今天的地位?就是因为她的笑!她的笑,带着股孩子的纯真,可以让别人对她丝毫不加提防,可以让人低估了她的力量与手段,也可以让别人毫无怨言地替她卖命!”
金叶侧首看着他,“你究竟是谁?怎么对李斜阳这么清楚?”
他微微一笑,却没说什么,低下头专心看信,看完之后,抬头打量金叶许久,脸上神情甚是惊异。
金叶不由自主伸手在脸上摸了一把,问:“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脸上长花了么?”
他摇了摇头,道:“原来,你竟是神谷子弟。”
金叶万没想到李斜阳给他的信中,竟会说了自己的身份,一时心下极为狐疑,将这两人一言一行又细细捉摸了一遍,蓦然脑中灵光一闪,也不急推敲,已失声道:“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胜――传――烽!”
那人也想不到她这样就能猜出自己身份,张口结舌愣了好一会,才正容道:“不错,我就是胜传烽,你千方百计地找我,就为了你们的《胜传烽传》么?”
金叶道:“不错。我是‘神谷’弟子,此次同几位兄长出谷,目的就在于撰写《胜传烽传》。胜先生的出身来历江湖上各种传言,莫衷一是,‘神谷’作传秉的是史家春秋之笔,故不揣冒昧,想请胜先生明告。”
胜传烽道:“神谷是不是人太多没有事情做?《胜传烽传》?我还没死呢。”
金叶轻轻一笑,“不一定非要死人才能立传的。”
胜传烽想了想,又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写《李斜阳传》?我胜传烽所做的事无一不与堂主有关。”
金叶道:“这就是‘神谷’的事了,不劳费心。”
胜传烽沉吟良久,方道:“我考虑一下,不过,你都写了点什么得先让我看看。我的出身来历,也许可以直接写给你们,但是要你们回到神谷之后方可启看。”
金叶笑道:“那没问题,不过底稿在我七哥那,先要见到我七哥才行。”
胜传烽望着他,“你说他们会去斜阳堂等容潇湘?李斜阳知道这些事吗?”
金叶点了点头,“我和她说了。”
胜传烽追问道:“她对容潇湘他们……有什么表示?”
金叶道:“当时她皱了皱眉,说:‘这倒是天意如此了!我见他们,必拼个你死我活,若是我死,这时毫无准备,胜传烽不见得能统御诸人,斜阳堂将要大乱。关中之乱,我本来在为是自己去还是让胜传烽去烦恼,吴川之叛,我和传烽皆可平,只是方式不同……这样一看,倒还是我去吧。你见到胜传烽,不妨把这话转告他。再告诉他,我知道这样也是难为他,可是,我相信以他的武功智慧,当不致有失。’然后她写了那封信,就带着几个人行色匆匆地走了。”
胜传烽诧异道:“你知道吴川将叛?”
金叶点点头,“李斜阳是当着我面接到这个消息的。”顿了顿,她忽然想到什么,奇怪地看了一眼胜传烽,道:“咦,昨天晚上我一说容潇湘和秋海蔚要杀李斜阳清理门户,你怎么就知道她出身秋水长天阁了?一般江湖中人,不应该知道有这么个门派的。”
“这……”胜传烽一时竟为之语塞。
金叶又想了想,道:“奇怪,你听到容潇湘这事,应该马上回斜阳堂才对,可是你怎么连一点都不急?”
胜传烽冷笑一声,“我急什么?我虽未见过堂主出手,可我知道在秋水长天阁最得阁主真传的并不是秋海蔚,更不是容潇湘,而是三个大弟子中另一人。”
金叶倒抽一口冷气,“你对秋水长天阁这么清楚!你是不是真的就是胜箫?胜箫死于六年前,斜阳堂创立于五年前,胜传烽也出现于五年前,时间上可吻合得很。”
胜传烽一笑道:“我的来历是我考虑要不要告诉你的事,你那么急打听干什么?”
斜阳堂。
容潇湘站在斜阳堂前,看着面前雕梁画栋的建筑和大门前挂着的“斜阳堂”的匾额,忍不住叹了口气,向秋海蔚道:“如此古朴雄伟的建筑,一看就知道必出于李斜阳设计;如此飘逸苍劲的字迹,一看就知道必出于李斜阳手笔……我虽一向和李师妹不睦,可我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胸怀才具。”
秋海蔚站在斜阳堂前,看着面前出于李斜阳设计的建筑和出于李斜阳手笔的匾额,忍不住也叹了口气,他眼中本就带着一股浓重的无奈和悲痛,此时更平添一份黯然伤魂。
“容潇湘,你站住!”容潇湘和秋海蔚方要抬步,蓦听得有人断喝一声,随即三个男子闪身挡在两人身前,正是“神谷”那三个弟子。
“七哥”抱拳道:“胜夫人,秋大侠,昨天的事四哥已经和我们说了,这件事如何解决,我们想听听二位的意思。”
容潇湘木然道:“你们划下道来,我接着就是,何必假客气?”
“七哥”看了一眼秋海蔚,“我们的意思,这件事是我们金家的人和你胜夫人之间解决,还是神谷和秋水长天阁之间了断?”
容潇湘冷冷道:“你们既不念师门数代交谊,秋水长天阁也不见得就怕了神谷。”
秋海蔚听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忍不住插言道:“三位,昨日之事纯属意外,何必……”
“四哥”冷笑一声道:“秋大侠,我敬你素日侠义无双,可想不到你竟也说这种风凉话!”
秋海蔚道:“这怎么是风凉话?昨天的事,你们这里也不是没人在场,那不是意外是什么?虽说各位有丧妹之痛,却也不能定说是我师姐害死令妹的。”
“三哥”道:“老七,和他们多说什么,我就不信我们还怕了他们!”
“七哥”皱眉道:“这么说,秋大侠是不肯置身事外了?”
秋海蔚看看容潇湘,她脸上仍是漠无表情,他长叹一声,道:“师姐有事,师弟自当服其劳。”
“七哥”道:“好!二位请,九妹在何处遇难的,我们就在哪里了断。”
容潇湘冷哼一声,转身刚要走,忽听斜阳堂内有个女子高声叫道:“等一等!”
金氏兄弟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正匆匆跑下台阶,向他们奔来,正是金叶。
三人又惊又喜,忙迎上前去,少不得一番问长问短。
金叶向斜阳堂门前一指,道:“是他救了我。”
斜阳堂大门之前,牌匾之下,有个男子正负手而立,脸上带着股似笑非笑的神情,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却仿佛与他们隔得极远极远,完全是在两个世界中似的。
“七哥”抱拳道:“多谢相救舍妹,不敢请教先生尊姓大名?”
那人微微一笑,拱了拱手,“在下胜传烽。”
秋海蔚听得“胜传烽”三字,心猛然间一紧,霍然抬头,他看着胜传烽,怎么也难以相信,这男子竟就是自己听说了多少次的胜传烽——
“李斜阳竟然选中这么丑的男子?”
“胜传烽居然如此潇洒?”
“他究竟是不是未死的胜箫?”
“李斜阳到底是否真和他不清不白?”
“李斜阳是和他逢场作戏呢还是真的喜欢他?”
“……”
秋海蔚看着胜传烽,心中各种念头纷至沓来,一时呆了。
金氏兄弟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费尽心血打探的胜传烽竟会这样被他们碰上,一时竟也说不出话来。
胜传烽扫了一眼门前这些人,忍不住笑道:“你们怎么都不说话?”
容潇湘脸色难看至极,她嘎声问:“你姓胜?”
胜传烽点头道:“不错。容女侠有何见教么?”
容潇湘道:“你和胜箫有什么关系?”
胜传烽道:“他姓胜,我也姓胜,如此而已。”
容潇湘追问道:“没别的关系了么?”
胜传烽脸色一冷,“当然。”
容潇湘却咬着牙一字字道:“我——不——信!”顿了顿,她道:“昨天我就看你眼熟,只是想不起来你象谁。你和胜箫都姓胜,长得也很象,连声音都差不多,你敢说你们没别的关系?”
胜传烽嘴角一斜,“信不信由你,我没功夫和你争论这些。各位在斜阳堂门前,有事要找斜阳堂么?没事就请便吧。”
“七哥”看一眼金叶,金叶低声向他说了些什么,他颇感意外地抬头看了一眼胜传烽,便取出一叠稿子交给金叶,一边道:“我昨晚修改了一些,又重新誊了一遍,胜先生肯指教,那是最好。”
金叶将这叠稿子捧到胜传烽面前,胜传烽接了交给身后一人道:“送到我屋里去,小心点,别弄乱了。”那人应了,退下。
容潇湘道:“我们要见你们堂主。”
胜传烽道:“对不起,堂主不在。”
容潇湘脸色一寒,“胜传烽,你也是江湖上有名有姓的人物,怎么当面撒谎?”
胜传烽沉着脸道:“我如何当面撒谎了?堂主在不在,是你知道还是我知道?”
容潇湘眉一沉,道:“就算她不在,我们也要在斜阳堂等她,等到她在为止!”
胜传烽斜眼瞅着她,“你们在斜阳堂等?凭什么?”
“我是她师姐,秋海蔚是她师兄。”
“对不起,我不知道堂主有没有你们这两位师兄师姐,恕我不敢招待。”
容潇湘怒道:“胜传烽,你简直是在耍无赖!”
胜传烽冷冷一笑,“我这是维护斜阳堂。否则,任什么人空口白话说一句自己是谁的师兄师姐就能进斜阳堂,斜阳堂早就被洗劫一空了。”
“什么?”容潇湘益怒,“你竟指我们为强盗?”
“我可没这个意思。不过既然容女侠已自承为强盗,斜阳堂就更不敢招待了。”
容潇湘瞪着他,眼睛里如要冒出火来,胜传烽却只是嘴角挂着个冷诮的笑,斜眼瞅着她。
“胜先生——”就在两人僵持之际,“七哥”忽地插言道,“我们可以证明,他们二位,确实是李堂主的师兄师姐。”
胜传烽的笑容更为冷诮,他打了个哈哈,道:“既然‘神谷’高足肯作证,我可倒不好意思再难为二位了。如此,几位都请到大厅奉茶。”
胜传烽将五人让入大厅,分别落座之后,“七哥”向胜传烽道:“胜先生,‘神谷’交稿之期为夏至之日……”
胜传烽一笑,“我知道……这样吧,今晚我来拜访金七先生如何?”
“七哥”点了点头道:“那就烦劳胜先生了。我们住在斜阳堂对面的云来客栈里,今晚恭候胜先生大驾。另外——”他看了金叶一眼,道:“我等有一不情之请,不知胜先生肯不肯俯允。”
胜传烽道:“是不是金姑娘有伤在身,不宜旅途劳顿,七先生想让她在斜阳堂住一段日子?”
“七哥”一愣,道:“不错。”
胜传烽笑道:“平日里,就想请‘神谷’高足来作客,亦不可得,而今难得可以为金姑娘效劳,我等真是求之不得,又怎么会不肯?……金姑娘在此,也正好可以看看堂主和秋大侠之战,不妨多住两日。”
“七哥”听了胜传烽最后那句话,脸上不由一红,他心里,正是想让金叶留在此地一睹李斜阳与秋海蔚的决战的,却不料胜传烽一语便道破了他的用意。他坐在那里,讪讪地有些不是滋味,便与“四哥”“五哥”借故告辞了。
月明中天,夜深人不寐。
金叶知道胜传烽曾在他们的底稿上作了些加注修改,可是他究竟写了些什么,她也并不知情。
她看着三位兄长相携离去,听着马蹄声踏着西北的风沙渐行渐远,心里,不由得一阵凄惶,觉得自己,孤独无助起来。
这时,胜传烽在她身旁柔声道:“金姑娘,回去吧。令兄他们,很快就会回来接你,你安心在斜阳堂住着,若缺什么,也尽管说。如果觉得孤单,斜阳堂中也有不少女子,我可以找人来陪伴姑娘……”
金叶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却又立时低下头去,想起自己所写《胜传烽传》中的一段:“人以其城府甚深,号之曰‘青蛇’。蛇者,阴毒之物也,人恒厌之。传烽处世,虽圆通明理而终乏诚恳之意,故友之长远者,唯二三人耳。传烽尝助峨嵋报黄夕、秦可之仇,初时诸女感激,然后方知其所为者,秦可所遗拳剑也,终鄙弃之。传烽尝与方骏善,骏有难,传烽助之,然多怨言,骏虽不怿而不能言,后骏私一女,传烽见之,悦其色,戏之,骏无可忍,终与断义……”她心里一阵惊竦,却隐隐约约地,开始怀疑起那些“三哥”“四哥”亲自调查取证的事的真实性来。
两人缓缓走向斜阳堂,却发觉,不知何时,斜阳堂门前,竟站了一个瘦削伶仃的人。
胜传烽仔细打量了他两眼,才迟疑地道:“是……秋大侠?”
那人“嗯”了一声,“我是秋海蔚。”
胜传烽眼中泛起一抹惊警之色,“那么晚了,秋大侠还不睡么?”
秋海蔚沉默许久,终于长叹一声,道:“你知道,李斜阳是我什么人吗?”
胜传烽与金叶俱自一愣,对视一眼,金叶道:“你们不是要清理门户么?难道,难道……她不是原名李青竹后改名李斜阳的秋水长天阁第三弟子?”
秋海蔚干笑一声,“原来,‘神谷’对秋水长天阁的事,的确不了解。不错,她是我三师妹,可是……”
他顿了顿,直视着胜传烽,接道:“她也是我的妻子。十年之前,我已曾为她与胜箫一战。”
胜传烽倒抽了一口冷气,脸色愈发显得惨白,可他双眼中却闪起了一道炽芒。他笑了笑,说:“这么说,秋大侠今晚,是想与胜某决一胜负,甚至,定出生死了?”
秋海蔚迟疑了一下,却说:“我……不知道。”他有些失神的眼光瞥着胜传烽,踌躇良久,终于悄然问:“你和她,真的……?”
胜传烽肯定地点了点头。
秋海蔚默然不语。
却听一阵笑声自长街另一头传来,随即响起一个男子沙哑的声音,“真是天公不知人间事。今夜不应明月当空,想此情此景,若是狂风大作,响几声霹雳,才不负长街对决之慨。”
三人一齐转头,却见长街外,一个形容落拓的汉子,一手执着酒葫芦,一手提一条长鞭,边喝边行,脸上已有三分醉色。
他也不看三人,又兀自道:“想当年,姑苏一战,秋海蔚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胜箫又是何等的豪情胜概,虽是暴雨滂沱,天下英雄今日思之,也振奋不已。想不到十年之后……嘿嘿……”
他毫不理会三人的目光,穿过长街,便消失在了黑暗中。
胜传烽望着他背影消失之处,喃喃道:“又是他!”
金叶先是一阵惊异,其后却恍然大悟,她曾写过这个人:“其人(胜传烽)性风流,裙钗中常有薄幸名。七年,出洛阳,拐张氏妇,燕好七日,发金归之。妇羞恚交秉,自缢于慈云庵。其夫洛阳武师王易庭,欲制传烽死命不得,迁居斜阳堂前,每有风吹草动,辄行挑唆,必使传烽应战尔罢。传烽怒,欲杀,而斜阳不许。”
这个汉子,大约便是那洛阳武师王易庭了。
秋海蔚望着他背影消失之处,却渐渐握紧了双拳。他蓦然回头,向胜传烽道:“胜先生,按理,我不该在主人未归时便生事端,只是,你我之间的事,若等斜阳回来,只怕更难了结……”
胜传烽冷冷一笑,打断他的话道:“不错,无论是我和堂主有染,还是因为秋大侠要杀堂主,我们这一场,是迟早要决的。那么,秋大侠,请。”
秋海蔚苦笑着点了点头,“好,胜先生,请。”
金叶悄悄退开几步,她能感觉到,这街上的气氛已全然变了,空气在瞬间绷紧得仿佛天地都已是死的一般。
山雨欲来风满楼。
剑风乍起。
胜传烽终于出手。
秋海蔚心头一震——这剑气,他很熟悉——在他成名之战中,他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剑气!
十年以来,他无时或忘。
虽然胜传烽的招式奇特而诡异,为他生平仅见,可那剑气,却正是他十年来思之依然不安的——胜箫的剑气!
金叶在“神谷”,是读过十年前姑苏城外那一战的记载的。
那时的胜箫,已是名满天下的青年剑客,“白马啸啸,素剑朗朗,醉倚红楼,起振云霄”,不知羡煞了多少豪杰,倾倒了多少红妆。
而当时的秋海蔚,则尚籍籍无名于江湖,但“姿容澹然而不改其神飞风越,寒衣简服而不掩其意夺天地”,气势骎骎然,叫人意为之折。
故此,那一战,又被誉为“秋意胜概”。
两人之战,“飞虹四坠,霹雳两分,千古豪杰为之气咽,天下英雄为之色变。幽冥为之噤声,天光为之凝滞,彼野萧萧,彼心凄凄,不尽急雨,玉碎瓦全。”
这一战,两人都受了不轻的伤,但直至血染征衣,也还是平分秋色。
这一战之后,秋海蔚声名鹊起,胜箫更由此列身天下七大名剑。
这一战,人们至今犹为传颂。
秋海蔚胜传烽交手三招。
三招中,胜传烽的剑气虽然冷削,秋海蔚却始终不曾拔剑。
胜传烽却仍毫不留情,一剑快似一剑,一剑狠似一剑,每一剑,秋海蔚都是在间不容发间避了开去的。
终于,秋海蔚手中清啸声起,一道眩目的光华闪过,胜传烽手中长剑铮然而断。秋海蔚手中的剑进而点在胜传烽咽喉之上。
两人四目交投,谁也不出声,胜传烽眼中,隐隐流露出一股不甘不服之色。
与此同时,金叶失声惊呼:“秋情玉魄剑!”
秋海蔚手中握的,是一柄长约一尺七分,通体晶莹剔透的玉剑,剑虽光华润泽而明艳,却依然让人觉得怆然无比。
秋海蔚凝视着胜传烽,心中不知转过了几千几百个念头,终于还是长叹一声,缓缓收剑入鞘。
胜传烽看着他,淡然道:“这只是你的剑不平常,并不是你胜过了我。”他向金叶招了招手,“金姑娘,我送你回房。”
金叶看了一眼秋海蔚,轻声道:“秋大侠,我先走了。”低下头,随胜箫而去。
两人正要跨进斜阳堂大门时,胜传烽忽又停步,回头向秋海蔚道:“秋大侠,你进门的时候,烦劳关一下门,多谢了。”
秋海蔚木然站在街心,不知过了多久,耳边响起一个冷冰冰的女子声音:“你为什么不杀他?”
秋海蔚缓缓转身,看着容潇湘,“因为,他是胜箫。”
容潇湘迎着他的目光,冷然道:“那你就更该杀了他。”
秋海蔚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点什么,也不想逼师姐说给我听……对我来说,十年前,与胜箫一战之后,胜过胜箫,便成了我最大的心愿……我并非不想杀她,可是,我也希望,能公平决战。”
他顿了顿,又道:“何况,这毕竟是斜阳一手创办的基业,如今她不在堂中,我若杀了胜传烽,形势立将大乱……”
容潇湘冷笑一声,“不错,你若杀了她的姘头,可怎么向她交代!她会恨你一辈子,再也不回你身旁……”
秋海蔚脸色刹时铁青。
容潇湘却不理他,冷冷一笑,回身向斜阳堂走去,边走边道:“你不肯杀他,我自己也一样可以杀他,希望,他有命等到你们公平决战那一天吧!”
第一章完(1997年起稿,2002年完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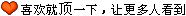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