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下午3时,启烽在监狱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人生苦旅。
除凤霞已经失踪外,启烽是全班第二个被死神拥抱的同学。第一个是安坤,1992年死于谋杀。因安坤当时是公安干警,身份特殊,谋杀时佩枪又被劫走,被公安部列为一级督办案件。十多年过去后,专案组虽然还在挂着,却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案件毫无进展。
如果说安坤的死,有其自身性格和社会治安方面的原因,则启烽的死,一些执法部门的冷酷和教条难辞其咎。
启烽的突然死亡,对其亲属打击很大。为了讨个说法,其妹罗丽到省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不同意将遗体火化。启烽的遗体,便还在殡仪馆摆着。
2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当时我正走在街上,人声噪杂,电话里的声音沙哑,我竟听不出是谁来。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回拨过去,才知道给我打电话的人是启烽。他说目前遇到困难,希望我在经济上给予援助,借点钱给他渡过难关。细问之下他才告诉我,他淋巴上长有个拳头大的肿瘤,需要手术切除,大约要五、六千元的费用。他要我先设法筹点钱给他,等他出狱后慢慢还我。
启烽未出事前,我们就很少联系,入狱后更是没有音信往来。前年虽和几个同学到监狱探视过他,并给他捐助了些生活费用,但却没有给他留下联系电话。而他却能在狱中查到我的电话号码,倒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五、六千元的款项,虽不是什么大数,单凭我一人却也负担不起。前年下半年沦为房奴后,每月的房贷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加上赴美的行期基本敲定,经费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这段时间我都在为钱的事发愁呢。但出于同学之义,启烽的困难我不能不管。他在最困难、最无奈的时候能想到我,足以说明他对我的期盼和信任。得到一个落魄之人的信任不容易,我还真不能辜负了他。
把启烽的情况告诉身边的几个同学,他们均觉得单凭几个人筹款有些困难。他们的经济情况,与我不相上下,都是属于收入偏少的工薪阶层,手头并不宽裕,除了吃穿用度、养儿育女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多余的钱款。加上大家对借钱给启烽将来能不能如数归还也心存疑虑,即使可以归还,只怕也是遥遥无期。个中关节,彼此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心中都是透亮着的,我自然不好勉强。于是有人提议由我牵头,组织理事会向全班同学募捐,不足部分再另外设法解决。
大学毕业后,大多数同学都已经失去联系。能不能和各地的同学联系上,联系上后有没有人响应,我们均没有把握。为此,我们设定了捐款金额不少于200元的底线。令我感动的事,捐助倡议发出去后,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积极响应。在我赴美之前,全班已经有34名同学为启烽捐款,之后又有4名同学陆续把捐款寄来。迄今为止,共有38名同学为启烽捐款,总计金额18000元,是启烽最初希望资助金额的3倍。我想,同学们除了对启烽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怜悯外,还有对我这个老班长的信任。
2月中旬,我约了同学到监狱探视启烽,告诉了我们为他筹备捐款的情况,并鼓励他调整情绪,放松精神,积极和病魔作斗争。启烽到州医院诊断治疗期间,我们代表全班同学再次探视了他。然而,启烽的病情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他也没有预料到自己患的竟是绝症。经骨髓穿刺化验,启烽患的竟是白血病。淋巴上的肿瘤,系患白血病后免疫功能低下,由牙龈发炎引起。
确诊后,罗丽即向监狱方面申请办理取保就医手续。因其在省公安厅有熟人,且愿意帮她到省监狱管理局疏通,以为取保就医手续最多一个星期就可以办下来,清醒颇为乐观。罗丽经与广州方面的有关专家联系,认为启烽的病情尚可挽救,但要尽快送去。因启烽病体虚弱,乘飞机或坐火车到广州都不可能。按照当时的设想,先将启烽带到贵阳医学院进行细胞隔离手术,待体力恢复后,再转至广州医治。在州医院治疗期间,启烽每天的医药费用就高达2000多元,要到贵阳和广州治疗,同学们的这些捐款自然远远不够。经启烽同意,其家人准备把住房卖掉,先筹款治病再说。
3月4日,我们代表全班同学同学把筹到的捐款交给了罗丽。随后,我嘱咐在家的同学继续关注启烽的病情和捐款情况,即随团前往美国。回来后,还没来得及理清思绪,待要过问启烽治疗的情况时,竟收到他在监狱病死的消息。细问方知,省监狱管理局一直没有把启烽取保就医的手续批下来。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启烽一直被关在监狱,没有得到起码的治疗。由于病情延误,并不断恶化,启烽终于凄凉地死在了监狱。启烽辞世时,身边一个亲人送终都没有。启烽的家人获悉噩耗,自是悲痛莫名,他们要向有关方面讨个说法,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启烽个子不高,平时也不怎么言笑。他写字总是一丝不苟,绝不像我这般潦草。启烽是在大学入的党,并担任我们班的支部书记,还是系支部和学生会的什么委员。或许是入党时过于年轻,又时刻想着保持党员形象,大学时代的启烽,为人未免有些刻板,一如他的字体一般。我当时虽然担任班长,和启烽的关系却有些芥蒂。在校期间,我不仅是学院的优秀团员和优秀班干,学习成绩在班上也名列前茅,自身条件不可谓不好。然而我提交的入党申请,在启烽主持的支部会上却没有被通过。当时我并不怎么懂政治,内心也不把入党当作什么大不了的事,恼就恼在班上一些稍微有些姿色的女同学,都被启烽介绍入了党,偏偏把我拒之门外。因此,心里对启烽颇有微词,对其行为更是不屑。大学毕业前后,便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疏远他。在我带工作组到麻江驻村开展扶贫帮困工作以前,与启烽一直没有联系和来往。
启烽大学毕业后比我幸运,凭其在校期间积极要求进步这块招牌,一毕业就进了县委组织部。当他到发改局出任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时(当时该局缺局长),我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并被委派到他治下的一个村开展扶贫帮困工作。为村民修建沼气池的事,我带工作组的同志到发改局找启烽帮忙,他免费给我们提供了10吨水泥,总算尽了同学之谊。
听说启烽是在发改局主持工作期间出的事。那时,凯麻高速公路正在修建,大部分建设项目在麻江。作为发改局长,启烽当时可谓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凯麻高速公路修成后,麻江县倒下了一批干部,启烽就是其中之一。我不知道启烽究竟受贿多少,按他的性格和为人,充其量也就是个从犯,但他居然被判了13年徒刑。传说对他量刑有些偏重,而且不该由他承担的罪责,他也主动承担了下来,好像是为了保某个人物。当然,这都是小道消息,不足为据。
正是因为有了在麻江支持我开展帮扶工作的交情和同学故旧之谊,启烽在落魄之时,终于想起向我这个当年的老班长求助。得益于同学们的支持,我有幸不曾让启烽失望。然而,同学们的关心支持,毕竟还是挽救不了启烽的性命。这是启烽的悲哀,也是当代司法制度的悲哀。
除凤霞已经失踪外,启烽是全班第二个被死神拥抱的同学。第一个是安坤,1992年死于谋杀。因安坤当时是公安干警,身份特殊,谋杀时佩枪又被劫走,被公安部列为一级督办案件。十多年过去后,专案组虽然还在挂着,却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案件毫无进展。
如果说安坤的死,有其自身性格和社会治安方面的原因,则启烽的死,一些执法部门的冷酷和教条难辞其咎。
启烽的突然死亡,对其亲属打击很大。为了讨个说法,其妹罗丽到省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不同意将遗体火化。启烽的遗体,便还在殡仪馆摆着。
2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当时我正走在街上,人声噪杂,电话里的声音沙哑,我竟听不出是谁来。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回拨过去,才知道给我打电话的人是启烽。他说目前遇到困难,希望我在经济上给予援助,借点钱给他渡过难关。细问之下他才告诉我,他淋巴上长有个拳头大的肿瘤,需要手术切除,大约要五、六千元的费用。他要我先设法筹点钱给他,等他出狱后慢慢还我。
启烽未出事前,我们就很少联系,入狱后更是没有音信往来。前年虽和几个同学到监狱探视过他,并给他捐助了些生活费用,但却没有给他留下联系电话。而他却能在狱中查到我的电话号码,倒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五、六千元的款项,虽不是什么大数,单凭我一人却也负担不起。前年下半年沦为房奴后,每月的房贷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加上赴美的行期基本敲定,经费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这段时间我都在为钱的事发愁呢。但出于同学之义,启烽的困难我不能不管。他在最困难、最无奈的时候能想到我,足以说明他对我的期盼和信任。得到一个落魄之人的信任不容易,我还真不能辜负了他。
把启烽的情况告诉身边的几个同学,他们均觉得单凭几个人筹款有些困难。他们的经济情况,与我不相上下,都是属于收入偏少的工薪阶层,手头并不宽裕,除了吃穿用度、养儿育女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多余的钱款。加上大家对借钱给启烽将来能不能如数归还也心存疑虑,即使可以归还,只怕也是遥遥无期。个中关节,彼此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心中都是透亮着的,我自然不好勉强。于是有人提议由我牵头,组织理事会向全班同学募捐,不足部分再另外设法解决。
大学毕业后,大多数同学都已经失去联系。能不能和各地的同学联系上,联系上后有没有人响应,我们均没有把握。为此,我们设定了捐款金额不少于200元的底线。令我感动的事,捐助倡议发出去后,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积极响应。在我赴美之前,全班已经有34名同学为启烽捐款,之后又有4名同学陆续把捐款寄来。迄今为止,共有38名同学为启烽捐款,总计金额18000元,是启烽最初希望资助金额的3倍。我想,同学们除了对启烽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怜悯外,还有对我这个老班长的信任。
2月中旬,我约了同学到监狱探视启烽,告诉了我们为他筹备捐款的情况,并鼓励他调整情绪,放松精神,积极和病魔作斗争。启烽到州医院诊断治疗期间,我们代表全班同学再次探视了他。然而,启烽的病情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他也没有预料到自己患的竟是绝症。经骨髓穿刺化验,启烽患的竟是白血病。淋巴上的肿瘤,系患白血病后免疫功能低下,由牙龈发炎引起。
确诊后,罗丽即向监狱方面申请办理取保就医手续。因其在省公安厅有熟人,且愿意帮她到省监狱管理局疏通,以为取保就医手续最多一个星期就可以办下来,清醒颇为乐观。罗丽经与广州方面的有关专家联系,认为启烽的病情尚可挽救,但要尽快送去。因启烽病体虚弱,乘飞机或坐火车到广州都不可能。按照当时的设想,先将启烽带到贵阳医学院进行细胞隔离手术,待体力恢复后,再转至广州医治。在州医院治疗期间,启烽每天的医药费用就高达2000多元,要到贵阳和广州治疗,同学们的这些捐款自然远远不够。经启烽同意,其家人准备把住房卖掉,先筹款治病再说。
3月4日,我们代表全班同学同学把筹到的捐款交给了罗丽。随后,我嘱咐在家的同学继续关注启烽的病情和捐款情况,即随团前往美国。回来后,还没来得及理清思绪,待要过问启烽治疗的情况时,竟收到他在监狱病死的消息。细问方知,省监狱管理局一直没有把启烽取保就医的手续批下来。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启烽一直被关在监狱,没有得到起码的治疗。由于病情延误,并不断恶化,启烽终于凄凉地死在了监狱。启烽辞世时,身边一个亲人送终都没有。启烽的家人获悉噩耗,自是悲痛莫名,他们要向有关方面讨个说法,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启烽个子不高,平时也不怎么言笑。他写字总是一丝不苟,绝不像我这般潦草。启烽是在大学入的党,并担任我们班的支部书记,还是系支部和学生会的什么委员。或许是入党时过于年轻,又时刻想着保持党员形象,大学时代的启烽,为人未免有些刻板,一如他的字体一般。我当时虽然担任班长,和启烽的关系却有些芥蒂。在校期间,我不仅是学院的优秀团员和优秀班干,学习成绩在班上也名列前茅,自身条件不可谓不好。然而我提交的入党申请,在启烽主持的支部会上却没有被通过。当时我并不怎么懂政治,内心也不把入党当作什么大不了的事,恼就恼在班上一些稍微有些姿色的女同学,都被启烽介绍入了党,偏偏把我拒之门外。因此,心里对启烽颇有微词,对其行为更是不屑。大学毕业前后,便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疏远他。在我带工作组到麻江驻村开展扶贫帮困工作以前,与启烽一直没有联系和来往。
启烽大学毕业后比我幸运,凭其在校期间积极要求进步这块招牌,一毕业就进了县委组织部。当他到发改局出任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时(当时该局缺局长),我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并被委派到他治下的一个村开展扶贫帮困工作。为村民修建沼气池的事,我带工作组的同志到发改局找启烽帮忙,他免费给我们提供了10吨水泥,总算尽了同学之谊。
听说启烽是在发改局主持工作期间出的事。那时,凯麻高速公路正在修建,大部分建设项目在麻江。作为发改局长,启烽当时可谓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凯麻高速公路修成后,麻江县倒下了一批干部,启烽就是其中之一。我不知道启烽究竟受贿多少,按他的性格和为人,充其量也就是个从犯,但他居然被判了13年徒刑。传说对他量刑有些偏重,而且不该由他承担的罪责,他也主动承担了下来,好像是为了保某个人物。当然,这都是小道消息,不足为据。
正是因为有了在麻江支持我开展帮扶工作的交情和同学故旧之谊,启烽在落魄之时,终于想起向我这个当年的老班长求助。得益于同学们的支持,我有幸不曾让启烽失望。然而,同学们的关心支持,毕竟还是挽救不了启烽的性命。这是启烽的悲哀,也是当代司法制度的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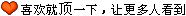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