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司法精神病学家孙东东教授近脚手架来正成为舆论炮轰的焦点。孙东东教授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需要实行强制治疗以保障人权。
老上访户至少99%以上有偏执型精神障碍,是一个统计,还是一个决定?孙东东教授“负责任地说”,更像是作了一个以学术权威身份担保的决定,而不是统计。
偏执型精神障碍是否必须强制治疗,是另一个问题。人类对精神病理现象所知还很肤浅,精神病治疗处在很不确定的水平。就算诊断准确,偏执型精神障碍中最严重的程度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也不至于言语紊乱、行为紊乱、情绪平淡,一般不危害公共安全。
孙东东教授首先作了老上访户99%以上有偏执型精神障碍的决定,然后又作了这种情况要强制治疗的决定。两个未必成立的决定,直接导出老上访户99%以上应当强制治疗的结论。这种勇猛,岂能与科学家的身份相称?
我不想以上访户的遭遇来反驳孙东东教授的立论了,也不推断孙东东教授的学术品格,其立论是否为着协助权力。我想,如果他的立论是独立的,那就更加值得深思,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作为一种权力,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脚手架到人们的生活。
在孙东东论老上访户的言论中,我们能够看到,知识(更准确地说,是挂有知识阶级徽章的结论)会直接决定一些人是获得自由还是被强制人身。在另外的场合,精神病诊断可以决定杀人者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知识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认识编码系统,一般而言,它被认为能够有效解释、定义、判断、预测事物及人类行为。而知识的言说,则由教授、专家等通常认为掌握了较多知识的人士进行。由此而形成“专家治理”,或者“技术治国”。它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精神病诊断、刑案处分、哪里要筑水坝、哪里要盖工厂、哪里要开矿山、吃什么样的添加剂等等,人们实际上已经将命运交给知识来判断,具体地说,委托给了各种不同的专家。
专家的话语权大小,决定了他影响我们生活的深度。我们之所以要喝这一种牛奶而不是那一种牛奶,可能只是在于某几个专家所作的决定。面粉中是否可以添加增白剂,就形成了一些专家说可以,一些专家说不可以的局面,而说可以的专家制定了标准,从而产生了法律效力,使我们能够吃上很白的面粉。
一定程度上说,“专家治理”或“技术治国”,抽空了民主的基础。专家不再是提供专业意见,向公众解释方案,并争取支持,而是直接定案。专家物料机
集团甚至某个专家,就可以直接行使权力。例如一个水坝修还是不修,可能直接涉及很多人的生活,涉及更多人的安全,但专家可以代你作主。知识是不断发展的,例如化肥使农作物增产,但不断加量施用的结果,使我们处在一个与化肥为伍的食物链中,这恶果并不是即时显现。
有的时候,专家径直决定获得了喝彩;有的时候,专家径直决定受到了抨击。然而,人们大多针对着喝彩与抨击和室
的具体决定,而很少去反思专家决断,知识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未被揭示。孙东东教授可以十分自负地决定99%以上的老上访户要强制治疗,乃是专家决断的一个例子而已,这种自负建立在“知识为王”的精神之上。
柏拉图的“哲人王”,由不同学科的“知识寡头”共同担当,这是部分知识人的梦想,他们也会指责权力对知识的干涉。“知识寡头”们在各自领域为权力意志背书,这是权力者的梦想。这两种梦想,都与民主没有什么关系。知识成为权力的仆从,人们知其大病,但逃出狼窝入虎口不是幸福,“知识为王”也须要当心。
老上访户至少99%以上有偏执型精神障碍,是一个统计,还是一个决定?孙东东教授“负责任地说”,更像是作了一个以学术权威身份担保的决定,而不是统计。
偏执型精神障碍是否必须强制治疗,是另一个问题。人类对精神病理现象所知还很肤浅,精神病治疗处在很不确定的水平。就算诊断准确,偏执型精神障碍中最严重的程度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也不至于言语紊乱、行为紊乱、情绪平淡,一般不危害公共安全。
孙东东教授首先作了老上访户99%以上有偏执型精神障碍的决定,然后又作了这种情况要强制治疗的决定。两个未必成立的决定,直接导出老上访户99%以上应当强制治疗的结论。这种勇猛,岂能与科学家的身份相称?
我不想以上访户的遭遇来反驳孙东东教授的立论了,也不推断孙东东教授的学术品格,其立论是否为着协助权力。我想,如果他的立论是独立的,那就更加值得深思,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作为一种权力,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脚手架到人们的生活。
在孙东东论老上访户的言论中,我们能够看到,知识(更准确地说,是挂有知识阶级徽章的结论)会直接决定一些人是获得自由还是被强制人身。在另外的场合,精神病诊断可以决定杀人者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知识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认识编码系统,一般而言,它被认为能够有效解释、定义、判断、预测事物及人类行为。而知识的言说,则由教授、专家等通常认为掌握了较多知识的人士进行。由此而形成“专家治理”,或者“技术治国”。它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精神病诊断、刑案处分、哪里要筑水坝、哪里要盖工厂、哪里要开矿山、吃什么样的添加剂等等,人们实际上已经将命运交给知识来判断,具体地说,委托给了各种不同的专家。
专家的话语权大小,决定了他影响我们生活的深度。我们之所以要喝这一种牛奶而不是那一种牛奶,可能只是在于某几个专家所作的决定。面粉中是否可以添加增白剂,就形成了一些专家说可以,一些专家说不可以的局面,而说可以的专家制定了标准,从而产生了法律效力,使我们能够吃上很白的面粉。
一定程度上说,“专家治理”或“技术治国”,抽空了民主的基础。专家不再是提供专业意见,向公众解释方案,并争取支持,而是直接定案。专家物料机
集团甚至某个专家,就可以直接行使权力。例如一个水坝修还是不修,可能直接涉及很多人的生活,涉及更多人的安全,但专家可以代你作主。知识是不断发展的,例如化肥使农作物增产,但不断加量施用的结果,使我们处在一个与化肥为伍的食物链中,这恶果并不是即时显现。
有的时候,专家径直决定获得了喝彩;有的时候,专家径直决定受到了抨击。然而,人们大多针对着喝彩与抨击和室
的具体决定,而很少去反思专家决断,知识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未被揭示。孙东东教授可以十分自负地决定99%以上的老上访户要强制治疗,乃是专家决断的一个例子而已,这种自负建立在“知识为王”的精神之上。
柏拉图的“哲人王”,由不同学科的“知识寡头”共同担当,这是部分知识人的梦想,他们也会指责权力对知识的干涉。“知识寡头”们在各自领域为权力意志背书,这是权力者的梦想。这两种梦想,都与民主没有什么关系。知识成为权力的仆从,人们知其大病,但逃出狼窝入虎口不是幸福,“知识为王”也须要当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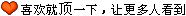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