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全面的,就转过来了,在中文站上看到的,不过好象也是转别人的:
五月天阿信:几乎每天都困在"文字狱"里(1)
有旋律配合,那就是歌词;那旋律抽掉,还能是诗。五月天的阿信,在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他写下的文字,不仅可以用来歌唱,还可以用来朗读。
写歌词有时就像在坐牢
《音乐周刊》:怎么想到要做这本书,把六年来所有的歌词结集?
阿信:我们在前不久做了自己的精选集,我就也想整理出这些文字。另外还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在抽掉了编曲和旋律之后,我相信我的文字还是经得起阅读的,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文字去感受歌词里面的一些东西。其实歌手做书的话,投资报酬率是非常低的,而且在出版的过程中发现在内地出简体版原来也有那么多的困难。
《音乐周刊》:用一本书的方式把所有的歌词放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图片,这样出书,不会觉得有点太水了吗?
阿信:我之前也担心会不会太水,但是公司同事和朋友多觉得不错,他们认为,如果你再回头去思考的话,这东西花了我六年的时间,只要是五月天不做宣传的日子,我几乎都是困在一种"文字狱"里面。所谓的"文字狱",我想做创作的人都了解,就是为了一首歌的一段,一举,有时就像在坐牢一样,一天不完成这个作品,你的头脑都没办法休息,总是在不断地琢磨,不断地找灵感。出这本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重新的肯定,在自己整理的过程中,我非常相信自己的创作是有价值的。我在前面做了一万字的序言,还包括了我个人的第一张单曲,所以买这本书还是很值得的,我们不会辜负那么多歌迷口袋里的零用钱。
《音乐周刊》:在作曲的过程中总是会感觉到困难吗?就像你刚才说的"文字狱"一样痛苦?
阿信:有时候,有些歌曲做起来是行云流水的,但是这种状况大概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多不那么顺利。就像人们有时问我们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我会说我们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都是在瓶颈中,因为所有的创作都是"炼金术",你要把生活中所接触的讯息,产生的喜怒哀乐,你的理想,你的呐喊,你的怒吼,你的开心和狂叫统统变成歌词那样的文字,我觉得这个精炼的过程其实是挺难的。
《音乐周刊》:是不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一瞬间的灵感来了,产生了几句非常好的歌词,但是很难把它继续下来,成为完整的歌词?
阿信:其实大部分时候,如果要写歌的话,那种状况我是非要把自己关起来不可的。有一首歌是我在大学里写的,那时我住在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是顶楼,没有冷气,还是铁皮屋,夏天的时候可以到45度,我关在里面三天三夜写出那首歌。现在没有那么多大块的时间,所以就慢慢训练自己在人群里自闭的功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可以把自己关在当年那个45度的铁皮屋,去投到自己的世界里创作。这也算是一种怪癖吧,有点自虐的倾向,但这又是一个通并快乐着的事情。(这个就是"爱情万岁")
我们都需要棍子与胡萝卜
《音乐周刊》:每次都要这样逼着自己创作吗?
阿信:我有一种好胜的性格,当看到其他顶尖的词作家能够写出很棒的歌词,我就会像,为什么?我想要超过他,我想写得比他更好,想要流传得更远更久。
《音乐周刊》:曾经想要超过谁?
阿信:只要你说得出来的,我都想超过。
《音乐周刊》:比如说方文山?
阿信:方文山是华人词作这里能一直激起我创作的野心的人,但我们应该是路线不同的。
《音乐周刊》:你们五个里不是玛莎文笔最好吗?
阿信:应该说我这本书要这么努力的出版,就是怕玛莎出书之后被他盖过。他的文笔非常好,但它是需要经纪人的棍子与胡萝卜的。你养过驴子就知道,胡萝卜在前面引诱,棍子在后面打他。我们就要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不过我猜他不会喜欢胡萝卜。看过他写的东西,你才会真的发现原来自己跟一个天才在一起,而他却始终是装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音乐周刊》:如果玛莎是天才,那你是什么?
阿信:我是一个拥有天才团员的乐队的主唱。我觉得Beatles之所以那么杰出,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有两个天才,保罗·麦卡尼和约翰·列侬,我相信这两个天才如果分属于两个团体,他们肯定不会那么精彩。
《音乐周刊》:那你们五月天内部呢,谁是保罗·麦卡尼,谁是约翰·列侬?
摇滚是一个剥离理智的过程
《音乐周刊》:这本书中,方文山说你的歌词是摇滚诗,可是当歌词脱离摇滚的旋律之后,又如何让人感受到摇滚的气质呢?
阿信:对我来说,摇滚是一个剥离理智的过程。我觉得我们长大成人所受的教育,很大的一块就是要把你的纯真,天真从身上活生生的连血带肉的给剥下来。那些东西对我,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很珍贵的。所谓的长大就是你变得世故,冷漠,圆滑,就像脚上长的茧子,穿了新鞋都不会痛。我自己的创作是一直在搜集那些被剥离下来的血肉,要逼着自己看那些心中原来是属于你但是现在已经残破的部分,其中也包括了很多要逼视自己的弱点的部分。除了迎合市场的那些情歌之外,你还会在我的书里看到很多无法实现的梦想,人生中遭遇的生离死别,甚至于青少年暴力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我的作品内容是很真实的,即使是不真实的想象,都还是可以找到人生中应对的部分。
《音乐周刊》:那你有没有逼视到自己的弱点?
阿信:有啊,我整个身上都是弱点。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是可以写出"咸鱼"这样孤立人生的作品,其实这种励志的歌很多人都在写。但是很容易写成口号的串联,写着写着自己都不知道在写什么,那种歌词是很空的。我希望写出更扎实的句子,如果我们受到诋毁,甚至承受了很多不该承受的烙印在身上,你要相信,"被火烧过的地方,才能成为凤凰。"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悲观很懒惰的人,我就是因为太懒惰了,总是要找借口,弱点一大堆,所以自己最知道怎么说服自己,所以可以写出"我的手越肮脏。眼生越是发光"这样的励志的句子。在出道之前,我曾经在室内设计的公司打工,盖房子,磨水泥我都做过,手虽然很脏,心里却沉甸甸的。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做过,才能够写出真实的东西。
喜欢岩井俊二,甜美的影响+有力的控诉
《音乐周刊》:这本书里还有你自己拍的照片,你平时很喜欢摄影?
阿信:我觉得数码相机出现后,每个人都可以使摄影时,对摄影师的定义就像诗人,你必须把你看到的东西精炼过。不过我用的都是随手拍的宝丽来。
《音乐周刊》:你的书除了自己的摄影之外,还特意请了岩井俊二的御用摄影师ivy chen,是你自己特别喜欢她所以邀请她吗?
阿信:应该说也是一种巧合,我们一直在选摄影师,同时也拿到了她的摄影作品集,我又是非常喜欢岩井俊二的电影,它的影响都很甜美,但是里面又有非常有力的控诉,是很真实的力量。我希望我这本书作出来,看起来干干净净,但内里是有些力量的。
《音乐周刊》:你最喜欢岩井俊二的哪部作品?
阿信:《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其实莉莉周的原型就是王菲,她本来是想在中国拍摄的,最后还是在日本拍。
《音乐周刊》:其实你的这本书也有点那部电影的感觉,很多明快的影像,中间夹杂着文字,是断断续续却又彼此连接。
阿信:你说我的书像他的电影那可真是太抬举我了。
五月天是在17岁那年被做成的果冻
《音乐周刊》:你们五个总是一起出现,现在一个人出来,会不习惯?
阿信:平时联访的时候,我是负责将场面话的,要不就是打游击,比如冠佑有漏洞的时候我就攻击他。
《音乐周刊》:五月天里已经有两个结婚了,算是从男孩成长到男人了,有没有想过今后的音乐道路?
阿信:首先,只要五月天理由怪兽和玛莎这两个家伙,就不可能从男孩变成男人。他们永远都是17岁,也许现在是17岁零两百多个月吧。我觉得五月天很有趣,我们从高中认识之后,就没有跟其他人组过乐团,也没有真正出过社会,没有在社会上和别人工作过,感觉就是17岁的时候被人做成了果冻,凝在里面。好处是不会烂掉,坏处是也很难变得更熟了。
《音乐周刊》:很多人说五月天的音乐是泡泡糖音乐?
阿信:泡泡糖就泡泡糖吧,至少年轻人愿意把它放在嘴里嚼。
《音乐周刊》:可是嚼完之后不久没味道了吗?
阿信:我相信五月天的音乐是不会变味的泡泡糖。我们总希望五月天的音乐能让人少长大一点,少世故一点,心脏外面少长一层茧子,感觉更容易对应该感动的事情感动,对应该难过的事情难过。即使未来在不同的岗位上,我都希望那些不长茧的心能够创造出让我们觉得更温暖的世界。我相信他们能把五月天的歌听进心里去,那是我们所谓的摇滚。至于我们会不会更摇滚,更长大成熟,也许会,也许不会。昨天看到怪兽看足球的样子,我觉得也许离变成真正的大人,还有一定的时间。
阿信:其他四个都有这样的潜力,基于这种情况,我把录音室里的纸和笔都藏起来了。
《音乐周刊》:你给别人写歌都有什么要求?
阿信:有些人找我写歌是随缘的态度,有些人就是抱着志在必得的态度,给我他们的棍子和胡萝卜,经常电话我打听今天我做了什么,我就不好意思说我今天跟朋友出去逛街,我会说我在写歌词,这样子就一定得及时写完交给人家。
希望可以戴上"作家"头衔
《音乐周刊》:有人说,诗不一定都可以作为歌词,但是每一首歌词都是诗,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阿信:我觉得不一定,歌曲比较好定义,但是你看最近经常在电视里的"美好时光海苔"那首广告歌,那是不是诗就会比较有争议了。
《音乐周刊》:你觉得你的歌词都是诗?
阿信的经纪人(插话):不是他觉得,我记得1999年李宗盛第一次看到阿信的歌词时,他就觉得像一首诗,他说阿信的歌词完全不一样,有特殊的人文气息。
阿信(猛地回头):他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音乐周刊》:你觉得你本人有没有诗人的气质?
阿信:什么是诗人的气质?所谓诗,应该是有文字上的美感,有想象力以及词句的跳跃等等。像我1999年写的《拥抱》这首歌,"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月光怎么能晒干眼泪呢?其实是说你这辈子都看不到我的好,这同时包含了控诉,包含了期望,包含了画面的感觉——月光下痴情的人,眼泪在不停的流着。我们写一首伤感的歌,不见得都要用控诉的文字,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苦,好像"我对你那么好,你却跟着别人跑。我对你那么忠心,你却那么无情"这种的,应该会使用更美更有想象力的方式。其实我很感谢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很早以前我们都是写在羊皮或树皮上,每写下一个字都非常珍贵,所以一路发展下来,华语的文字拥有了组合上的美感。华人的方块字像积木,展开来是无意义的方块,但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含义。
音乐周刊》:你平时写歌用电脑还是用纸?
阿信:我用竹片……哈哈,假的,我用电脑。
《音乐周刊》:你也说以后还会继续出书,那么下一本书也是这种方式吗?
阿信:目前还保密,不过希望下本书出来的时候,可以当之无愧的戴上"作家"的名号。我衷心希望脱掉五月天主唱的名号之后,你可以不喜欢五月天,但是还会喜欢阿信。
《音乐周刊》:你很喜欢"作家"这个名号?
阿信:每天晚上都付出那么多努力,当然希望面对大众的时候有更多的自信。每天晚上电视只能开着画面,不能听声音,像这样的夜晚我过了六年。
我对整个世界都好奇
《音乐周刊》:你都有哪些爱好呢?
阿信:我好像喜欢的东西蛮多的,却又好像什么都不喜欢。如果真的要讲,应该是看书吧。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只要是书就看,不过不看电话薄。比如前阵子看科幻小说,倪匡的《太平天国》,倪匡说太平天国的人都是外星人,真的吗?那我就去找来太平天国的传记来看,看完之后才知道倪匡瞎扯。然后看历史之后就看到人类的起源,就跑去看人类的演化,发现人类都是基因生成的,就去看基因的书,看到分子,就想到要去看分子,结果这又有关宇宙的形成,有很好奇。
《音乐周刊》:平时也读诗吗?
阿信: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心里有个考大学的动力,所以就努力离那个目标进一点。那个动力就是,在大学里,手里推着一部单车,旁边有个女孩,单车的篮子里放着一本诗集,那时我想象的大学生活。结果后来真的上了大学之后,找一些诗来看,才发现我离所谓的诗还挺远的,有点看不懂。后来慢慢队时产生兴趣,因为看了台湾一些有名的诗人的作品,还有西洋的一些诗人的作品。我觉得人都是可以读诗的,只要是那诗够简单又不会失去内涵的话。我自己是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音乐周刊》:最近也看世界杯吗?
阿信:我也是从上一届世界杯才开始看足球的。这段时间有机会的话就会跟怪兽一起看,没机会的话就把电视开着,完全脱离世界杯就没有朋友了。
《音乐周刊》:那你比较喜欢哪个队呢?
阿信:我希望中国队能赢。前几天看到一个笑话:韩国人问上帝,什么时候可以拿到世界冠军,上帝说五十年之后,韩国人说那我这辈子看不到了,就哭了。日本人问上帝什么时候可以拿冠军,上帝说一百年之后,日本人说我这辈子看不到了,就哭了。中国人问上帝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冠军,上帝哭了,说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就算是枉不能绝望,中国一定可以有那一天的。来源:粉丝网论坛
五月天阿信:几乎每天都困在"文字狱"里(1)
有旋律配合,那就是歌词;那旋律抽掉,还能是诗。五月天的阿信,在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他写下的文字,不仅可以用来歌唱,还可以用来朗读。
写歌词有时就像在坐牢
《音乐周刊》:怎么想到要做这本书,把六年来所有的歌词结集?
阿信:我们在前不久做了自己的精选集,我就也想整理出这些文字。另外还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在抽掉了编曲和旋律之后,我相信我的文字还是经得起阅读的,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文字去感受歌词里面的一些东西。其实歌手做书的话,投资报酬率是非常低的,而且在出版的过程中发现在内地出简体版原来也有那么多的困难。
《音乐周刊》:用一本书的方式把所有的歌词放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图片,这样出书,不会觉得有点太水了吗?
阿信:我之前也担心会不会太水,但是公司同事和朋友多觉得不错,他们认为,如果你再回头去思考的话,这东西花了我六年的时间,只要是五月天不做宣传的日子,我几乎都是困在一种"文字狱"里面。所谓的"文字狱",我想做创作的人都了解,就是为了一首歌的一段,一举,有时就像在坐牢一样,一天不完成这个作品,你的头脑都没办法休息,总是在不断地琢磨,不断地找灵感。出这本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重新的肯定,在自己整理的过程中,我非常相信自己的创作是有价值的。我在前面做了一万字的序言,还包括了我个人的第一张单曲,所以买这本书还是很值得的,我们不会辜负那么多歌迷口袋里的零用钱。
《音乐周刊》:在作曲的过程中总是会感觉到困难吗?就像你刚才说的"文字狱"一样痛苦?
阿信:有时候,有些歌曲做起来是行云流水的,但是这种状况大概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多不那么顺利。就像人们有时问我们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我会说我们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都是在瓶颈中,因为所有的创作都是"炼金术",你要把生活中所接触的讯息,产生的喜怒哀乐,你的理想,你的呐喊,你的怒吼,你的开心和狂叫统统变成歌词那样的文字,我觉得这个精炼的过程其实是挺难的。
《音乐周刊》:是不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一瞬间的灵感来了,产生了几句非常好的歌词,但是很难把它继续下来,成为完整的歌词?
阿信:其实大部分时候,如果要写歌的话,那种状况我是非要把自己关起来不可的。有一首歌是我在大学里写的,那时我住在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是顶楼,没有冷气,还是铁皮屋,夏天的时候可以到45度,我关在里面三天三夜写出那首歌。现在没有那么多大块的时间,所以就慢慢训练自己在人群里自闭的功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可以把自己关在当年那个45度的铁皮屋,去投到自己的世界里创作。这也算是一种怪癖吧,有点自虐的倾向,但这又是一个通并快乐着的事情。(这个就是"爱情万岁")
我们都需要棍子与胡萝卜
《音乐周刊》:每次都要这样逼着自己创作吗?
阿信:我有一种好胜的性格,当看到其他顶尖的词作家能够写出很棒的歌词,我就会像,为什么?我想要超过他,我想写得比他更好,想要流传得更远更久。
《音乐周刊》:曾经想要超过谁?
阿信:只要你说得出来的,我都想超过。
《音乐周刊》:比如说方文山?
阿信:方文山是华人词作这里能一直激起我创作的野心的人,但我们应该是路线不同的。
《音乐周刊》:你们五个里不是玛莎文笔最好吗?
阿信:应该说我这本书要这么努力的出版,就是怕玛莎出书之后被他盖过。他的文笔非常好,但它是需要经纪人的棍子与胡萝卜的。你养过驴子就知道,胡萝卜在前面引诱,棍子在后面打他。我们就要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不过我猜他不会喜欢胡萝卜。看过他写的东西,你才会真的发现原来自己跟一个天才在一起,而他却始终是装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音乐周刊》:如果玛莎是天才,那你是什么?
阿信:我是一个拥有天才团员的乐队的主唱。我觉得Beatles之所以那么杰出,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有两个天才,保罗·麦卡尼和约翰·列侬,我相信这两个天才如果分属于两个团体,他们肯定不会那么精彩。
《音乐周刊》:那你们五月天内部呢,谁是保罗·麦卡尼,谁是约翰·列侬?
摇滚是一个剥离理智的过程
《音乐周刊》:这本书中,方文山说你的歌词是摇滚诗,可是当歌词脱离摇滚的旋律之后,又如何让人感受到摇滚的气质呢?
阿信:对我来说,摇滚是一个剥离理智的过程。我觉得我们长大成人所受的教育,很大的一块就是要把你的纯真,天真从身上活生生的连血带肉的给剥下来。那些东西对我,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很珍贵的。所谓的长大就是你变得世故,冷漠,圆滑,就像脚上长的茧子,穿了新鞋都不会痛。我自己的创作是一直在搜集那些被剥离下来的血肉,要逼着自己看那些心中原来是属于你但是现在已经残破的部分,其中也包括了很多要逼视自己的弱点的部分。除了迎合市场的那些情歌之外,你还会在我的书里看到很多无法实现的梦想,人生中遭遇的生离死别,甚至于青少年暴力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我的作品内容是很真实的,即使是不真实的想象,都还是可以找到人生中应对的部分。
《音乐周刊》:那你有没有逼视到自己的弱点?
阿信:有啊,我整个身上都是弱点。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是可以写出"咸鱼"这样孤立人生的作品,其实这种励志的歌很多人都在写。但是很容易写成口号的串联,写着写着自己都不知道在写什么,那种歌词是很空的。我希望写出更扎实的句子,如果我们受到诋毁,甚至承受了很多不该承受的烙印在身上,你要相信,"被火烧过的地方,才能成为凤凰。"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悲观很懒惰的人,我就是因为太懒惰了,总是要找借口,弱点一大堆,所以自己最知道怎么说服自己,所以可以写出"我的手越肮脏。眼生越是发光"这样的励志的句子。在出道之前,我曾经在室内设计的公司打工,盖房子,磨水泥我都做过,手虽然很脏,心里却沉甸甸的。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做过,才能够写出真实的东西。
喜欢岩井俊二,甜美的影响+有力的控诉
《音乐周刊》:这本书里还有你自己拍的照片,你平时很喜欢摄影?
阿信:我觉得数码相机出现后,每个人都可以使摄影时,对摄影师的定义就像诗人,你必须把你看到的东西精炼过。不过我用的都是随手拍的宝丽来。
《音乐周刊》:你的书除了自己的摄影之外,还特意请了岩井俊二的御用摄影师ivy chen,是你自己特别喜欢她所以邀请她吗?
阿信:应该说也是一种巧合,我们一直在选摄影师,同时也拿到了她的摄影作品集,我又是非常喜欢岩井俊二的电影,它的影响都很甜美,但是里面又有非常有力的控诉,是很真实的力量。我希望我这本书作出来,看起来干干净净,但内里是有些力量的。
《音乐周刊》:你最喜欢岩井俊二的哪部作品?
阿信:《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其实莉莉周的原型就是王菲,她本来是想在中国拍摄的,最后还是在日本拍。
《音乐周刊》:其实你的这本书也有点那部电影的感觉,很多明快的影像,中间夹杂着文字,是断断续续却又彼此连接。
阿信:你说我的书像他的电影那可真是太抬举我了。
五月天是在17岁那年被做成的果冻
《音乐周刊》:你们五个总是一起出现,现在一个人出来,会不习惯?
阿信:平时联访的时候,我是负责将场面话的,要不就是打游击,比如冠佑有漏洞的时候我就攻击他。
《音乐周刊》:五月天里已经有两个结婚了,算是从男孩成长到男人了,有没有想过今后的音乐道路?
阿信:首先,只要五月天理由怪兽和玛莎这两个家伙,就不可能从男孩变成男人。他们永远都是17岁,也许现在是17岁零两百多个月吧。我觉得五月天很有趣,我们从高中认识之后,就没有跟其他人组过乐团,也没有真正出过社会,没有在社会上和别人工作过,感觉就是17岁的时候被人做成了果冻,凝在里面。好处是不会烂掉,坏处是也很难变得更熟了。
《音乐周刊》:很多人说五月天的音乐是泡泡糖音乐?
阿信:泡泡糖就泡泡糖吧,至少年轻人愿意把它放在嘴里嚼。
《音乐周刊》:可是嚼完之后不久没味道了吗?
阿信:我相信五月天的音乐是不会变味的泡泡糖。我们总希望五月天的音乐能让人少长大一点,少世故一点,心脏外面少长一层茧子,感觉更容易对应该感动的事情感动,对应该难过的事情难过。即使未来在不同的岗位上,我都希望那些不长茧的心能够创造出让我们觉得更温暖的世界。我相信他们能把五月天的歌听进心里去,那是我们所谓的摇滚。至于我们会不会更摇滚,更长大成熟,也许会,也许不会。昨天看到怪兽看足球的样子,我觉得也许离变成真正的大人,还有一定的时间。
阿信:其他四个都有这样的潜力,基于这种情况,我把录音室里的纸和笔都藏起来了。
《音乐周刊》:你给别人写歌都有什么要求?
阿信:有些人找我写歌是随缘的态度,有些人就是抱着志在必得的态度,给我他们的棍子和胡萝卜,经常电话我打听今天我做了什么,我就不好意思说我今天跟朋友出去逛街,我会说我在写歌词,这样子就一定得及时写完交给人家。
希望可以戴上"作家"头衔
《音乐周刊》:有人说,诗不一定都可以作为歌词,但是每一首歌词都是诗,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阿信:我觉得不一定,歌曲比较好定义,但是你看最近经常在电视里的"美好时光海苔"那首广告歌,那是不是诗就会比较有争议了。
《音乐周刊》:你觉得你的歌词都是诗?
阿信的经纪人(插话):不是他觉得,我记得1999年李宗盛第一次看到阿信的歌词时,他就觉得像一首诗,他说阿信的歌词完全不一样,有特殊的人文气息。
阿信(猛地回头):他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音乐周刊》:你觉得你本人有没有诗人的气质?
阿信:什么是诗人的气质?所谓诗,应该是有文字上的美感,有想象力以及词句的跳跃等等。像我1999年写的《拥抱》这首歌,"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月光怎么能晒干眼泪呢?其实是说你这辈子都看不到我的好,这同时包含了控诉,包含了期望,包含了画面的感觉——月光下痴情的人,眼泪在不停的流着。我们写一首伤感的歌,不见得都要用控诉的文字,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苦,好像"我对你那么好,你却跟着别人跑。我对你那么忠心,你却那么无情"这种的,应该会使用更美更有想象力的方式。其实我很感谢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很早以前我们都是写在羊皮或树皮上,每写下一个字都非常珍贵,所以一路发展下来,华语的文字拥有了组合上的美感。华人的方块字像积木,展开来是无意义的方块,但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含义。
音乐周刊》:你平时写歌用电脑还是用纸?
阿信:我用竹片……哈哈,假的,我用电脑。
《音乐周刊》:你也说以后还会继续出书,那么下一本书也是这种方式吗?
阿信:目前还保密,不过希望下本书出来的时候,可以当之无愧的戴上"作家"的名号。我衷心希望脱掉五月天主唱的名号之后,你可以不喜欢五月天,但是还会喜欢阿信。
《音乐周刊》:你很喜欢"作家"这个名号?
阿信:每天晚上都付出那么多努力,当然希望面对大众的时候有更多的自信。每天晚上电视只能开着画面,不能听声音,像这样的夜晚我过了六年。
我对整个世界都好奇
《音乐周刊》:你都有哪些爱好呢?
阿信:我好像喜欢的东西蛮多的,却又好像什么都不喜欢。如果真的要讲,应该是看书吧。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只要是书就看,不过不看电话薄。比如前阵子看科幻小说,倪匡的《太平天国》,倪匡说太平天国的人都是外星人,真的吗?那我就去找来太平天国的传记来看,看完之后才知道倪匡瞎扯。然后看历史之后就看到人类的起源,就跑去看人类的演化,发现人类都是基因生成的,就去看基因的书,看到分子,就想到要去看分子,结果这又有关宇宙的形成,有很好奇。
《音乐周刊》:平时也读诗吗?
阿信: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心里有个考大学的动力,所以就努力离那个目标进一点。那个动力就是,在大学里,手里推着一部单车,旁边有个女孩,单车的篮子里放着一本诗集,那时我想象的大学生活。结果后来真的上了大学之后,找一些诗来看,才发现我离所谓的诗还挺远的,有点看不懂。后来慢慢队时产生兴趣,因为看了台湾一些有名的诗人的作品,还有西洋的一些诗人的作品。我觉得人都是可以读诗的,只要是那诗够简单又不会失去内涵的话。我自己是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音乐周刊》:最近也看世界杯吗?
阿信:我也是从上一届世界杯才开始看足球的。这段时间有机会的话就会跟怪兽一起看,没机会的话就把电视开着,完全脱离世界杯就没有朋友了。
《音乐周刊》:那你比较喜欢哪个队呢?
阿信:我希望中国队能赢。前几天看到一个笑话:韩国人问上帝,什么时候可以拿到世界冠军,上帝说五十年之后,韩国人说那我这辈子看不到了,就哭了。日本人问上帝什么时候可以拿冠军,上帝说一百年之后,日本人说我这辈子看不到了,就哭了。中国人问上帝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冠军,上帝哭了,说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就算是枉不能绝望,中国一定可以有那一天的。来源:粉丝网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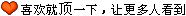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