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迷笛,选择硬梆梆的火车,选择小舞台,选择创意市集,选择跳蚤市场,选择软包装饮料,选择牛仔裤,选择翻墙而入,选择在太阳下暴晒几个小时,选择打口CD,选择诺基亚,不断地发短信,然后去会见那些未曾谋面但相识许久的朋友们,选择讨价还价,选择青岛啤酒或奉献爱心的中南海,要么低头聆听,要么冲进人群,选择在墙上写下自己的ID,选择其他的场地,来回奔波乐此不疲,选择在人群中选择自己。当四年前甚至更久以前的憧憬终究变成现实,你还会絮叨以往模糊不清的网络直播,责怪片面的文字和图片吗?就让那样的选择都见鬼去吧,而今这些都不是问题。
那么问题究竟是什么呢?人们所说的最糟糕的一届迷笛吗?还是昂贵的门票,依旧不合理的制度,又或者是突如其来的大雨和不景气的氛围?这些有那么重要吗,我们不过是亲爱的观众和热情的游客,在劳动节而来,都兴致勃勃地加入了这场聚会。
就让我跟随轰隆隆的火车皮而来,和一群热闹的伙伴玩捉弄人的飞鹰十三张,以打发漫长的旅途。尽管我不幸着凉拉了肚子,但这一切依然没能阻止年轻的人儿前行。是谁在怀念那间嘈杂的小平房呢,之前小家子气的冒险跟这次来比又算什么?于是,我们都摇着头说:“孩子,在迷笛音乐节散步才是正经事。”事实上,这并不是轻松的差事,不提毒辣辣的太阳,就说那潮湿的草地,让我们把屁股都往哪放,是用几本迷笛的小册子拼成屁股大小,还是索性让它潮湿下去?
结果,我那并不性感的屁股很不情愿地和草地来了一次又一次亲密接触,牛仔裤则干了又干,湿了又湿。写到这里,我必须插进一段鞋子的故事,因为它总是灰蒙蒙的,顺便见证了我的风尘仆仆。
那些未曾谋面的朋友也风尘仆仆地来了,他们戴着乖巧的墨镜,用遮阳伞,有的长出了一条尾巴,有的耳朵开在头顶上,他们做出各种姿态,因为短暂的时间双方放不开手脚,跟我一样因实际存在的陌生感到拘谨紧张,为了不让气氛过于尴尬,我们问寒问暖,露出一副心情愉快的表情。就这样那样待了一会,我们奔向各自的去处,或许一别永世。
还是去看演出吧,在各个舞台之前往返,不时地看手表和节目表,不可避免地顾此失彼,神经兮兮。在热爱的乐队面前留下眼泪,尽管他们不会留意眼皮底下某位青年的失态,或者混进人群里,像一个陀螺似的被撞来撞去。他们会说些激昂的话语,挑起人群的欢呼,爬上高高的铁架,在厕所门口和你来个碰面甚至合影留念。你接到丢下的龙虎人丹,跟着和“今年过节不收礼”的小调,一起撕破喉咙喊安可,对旁边和蔼陌生的人们微笑,成为别人的风景。我又偷偷地去了回小舞台,成为坐在地上的人们,甚至还偷偷打了个盹儿。你抱着吉他唱大屁股伯伯的时候我毫不吝啬自己的掌声,还笑了好多次。还有不死的八零年代,我们是低保真游戏的主角,在不安的噪音和缠绵的吉他音墙面前如痴如醉。至于你古怪的打扮,被摄进狭小的镜头里;瘦弱的身影,被写进日记;我甚至闭上双眼,在你无光的世界里遐想,感受那些沉默如谜的呼吸。
你累了吗,那就停下来抽一根软趴趴的烟,单手接住回旋飞盘,踢进世界波进球,放风筝,和老外练习口语,打量漂亮姑娘和小伙子,逗旁边的小孩子,发发牢骚,再赶往下一个地方。
音乐总是从别的地方而来,这听起来不太真切,就像我觉得自己有了足够的勇气从国际友人那抢下一口威士忌,抛弃了所有的不胜酒力和小心翼翼,也热烈地跟亲切的人们拥抱。我并没有去抽一根坚挺的香烟,躲在烟雾后面掩饰所有的神色匆匆、兴高采烈和冷峻。你还在胆小吗?惧怕所有激烈的撞击,又或者安于性格,把双脚钉在了地上,只在腿肚子发酸时不高兴地踢踢它。跟这些所有裹小脚的束缚说见鬼去吧,纵使单薄的排骨城居民缺乏强健的体魄,但又有什么能阻挡我在草地上打两个滚儿。既然喝啤酒爱变身,那么不妨来一盒怕上火的王老吉。
抱怨不是小姑娘才会唠叨的事情,就像埋怨不讲情面的太阳把皮肤晒黑了也不是小姑娘们的专利。那些轻松的复古迪斯科如此混沌,俨然是没到火候揭开锅的饺子;而观众中总有不和谐的声音响起,牛B果然是个牛B的词,正如傻B也是个傻B的词一般,总有不分青红皂白的使用者将它复杂的含义简单化。在听好音乐之前,是该好好学习中文,还是好好学习做人呢?不过我绝对不是苛刻的传教士,大可不必摆出严肃的面孔,但我还是想对那些乐队一成不变的发型和宣传专辑的话语皱皱眉头,然而怎么做是你们的,大不了我拍拍屁股转身离去。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小舞台的人们,他们大多时候安分地坐在草地上,压低声音说话,最多冲到前面蹦上几下。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这无可厚非。
就像你看腻了演出,不妨去创意市集上走走吧。我腼腆地索要名片,还碰到了腼腆的摊主。好奇的小虫子,你告诉我,这些复杂的针线活儿果真出自所有心灵手巧的小姑娘之手吗?而买一送一的黄瓜能给炎热的天气降温吗?你满手油彩,穿上独一无二的T恤,跟着火星叔叔来地球画下不知所云的图案,在胸前别上小巧的徽章,心里暗暗赞叹。要不你还可以去跳蚤市场串串,在途中索取免费的CD,跟着打击乐队一起把身体拧成麻花状,填写各式名单,跟碰上的乐手唠唠家常,唏嘘几下滑板小子,或许你来RAP那样也差不到哪去。
这些远远不是全部,你总会把某些敏锐的片段珍藏起来,独自一人分享。你也会有自己心中的结束,我记得那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它不过如年轻气盛的产物,远没有想象的那般伤感。也许这一切跟《Cult青年的选择》里的一个故事一样,我也在零七年的迷笛上被选中了,得以看到迷笛的真相。你变成怪物了吗,你需要去医院看医生吗,你的眼睛产生幻觉了吗?你是否因此失望,却又对来年寄予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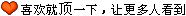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