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4年春天
地点:黑山渔庄
人物:阿彪(导演)
阿喜(摄影)
喜:对不起,下雨天难打车。你久等了。
彪:没事,我也才进来。傻逼保安非得让我付停车费,耽搁了一会儿。
喜:哇塞!你发了?刚买的车?什么牌的?
彪:喊什么喊,便宜货,POLO。
喜:你丫傍上富婆了吧?
彪:我倒是想啊。可惜没人看上咱这五短身材。给,这是上月问你借的钱。亲兄弟明算账。
喜:你看你??,嗨,不瞒你说,最近我手头特紧。给人拍了一个专题,一年多了还收不到钱。我恨不能把老板给劈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彪:这种事儿太多了,摊上自己就只好认倒霉。就当存在银行吧。慢慢来,别急。再说了,不是还有兄弟我嘛!
喜:那是那是!今后还得靠你多提携。对了,你今天怎么会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我从杨浦打车足足花了四十块钱!再说你也不吃辣呀?
彪:你知道这家店是谁开的吗?
喜:圈里谁不知道啊,神兵的老板呗。
彪:对!以前我也没来过。朋友有时候约我来,总觉得心里酸酸的。
喜:你和他有过节?
彪:没有。我甚至不认识富敏。我们是校友。主要是觉得自己没出息。你赶紧吃吧。鱼烧久了就老了。
喜:我把辣油捞了,你也吃一点儿?这鱼可是这里的招牌菜啊。
彪:我点了南瓜饼。苦日子过久了,就喜欢吃甜的。唉,今天你怎么没带咪咪来?
喜:上班去了。
彪:上班?不是不上班了吗?
喜:说来话长。咱们不说她,来,喝酒!
彪:我当时就劝过你,夜总会的女人只能玩,要不得的。
喜:嗨,咪咪人倒是不坏。只怪她想得太天真。我也一样。
彪:是啊,她怎么可能跟你过一辈子呢,川妹子出来目的很简单,就是挣钱。而你没钱。她不离开你才怪呢。要不要再来一瓶啤酒?
喜:好,再来一瓶。
彪:分手也好,迟早的事。好女人不多,波大的还怕找不到?
喜:话也不能这么说。这一年多我没少用她的钱。包括借给你的钱。
彪:啊,是这样啊。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喜:走一步看一步吧。你知道,我的活儿不多,找我的都是图省钱。我也知道自己也就是这么点本事。这还得感谢在电视台那几年偷学了几招。人家是不了解我才会请我。我说是北电学摄影的,大家都相信。提案本上还把我写成高才生甚至是资深摄影师,蒙谁呢?!那些傻逼在给钱的时候可不管你是什么东西。能少给就少给,能拖就拖。我要是指望他们真的相信我,那我才是傻逼呢!
彪:知道就好。不过这个行业真的不是很注重学历,我的书算是白读了!还是得靠自己啊!
喜:是啊是啊。彪哥你现在混得不错吧?
彪:我?还好吧。要不是你借给我钱,上个月我都快饿死了。
喜:其实当时你问我借钱的样子真不象穷人。我也装阔,兜里就剩两千了,给了你后直后悔。
彪:好兄弟,大哥不会忘记你的。天无绝人之路,这不,机会来了嘛。
喜:什么机会?
彪:前个礼拜天晚上我一个人无聊想去衡山路走走,在的士上捡到一个钱包。
喜:里面全是美金?
彪:只有三百元人民币。
喜:靠!
彪:你听我说完嘛。
,,,
喜:你知道我性子急。这不是人穷的时候见钱眼开嘛。
彪:我告诉你,人越穷越要注意吃相。这一点你不如我。正象你说的,上次问你借钱的时候我已经一整天没吃饭了。我却象没事一样。
喜:你丫水太深。要死的话绝不会是饿死的。我不行,要到那份上,只要能让我活,钻裤裆都成。
彪:你得改。有时候你要学会摆谱。过去我们都太老实了。我给你举个例子。马导演你该认识吧,有一次他接了一支六十多万预算的片子,制片公司答应给三万导演费。三万对当时还不怎么火而且正愁没钱结婚和打发小蜜的马导简直就是雪中送炭。按说他立刻就该答应才是。可人家就是牛逼。他一边说考虑考虑,一边让手下的小弟四处打听这个案子的背景。很快他就了解到这支片子的导演原来请的是台湾的钟梦宏,人家钟导可能是嫌钱少或者是排不开档期于是就随便向客户推荐了本地的马导。这下好了!人家马导一个电话打过去对制作公司说是谢谢关照,但最近状态不好想休息调整一下,片子还是不接了吧。还一个劲儿地道歉了一番。旁边的小弟听了直跳脚。我想,制作公司老板听了心里一定大骂你老马是什么东西啊,拍了几条破DV就以为自己是腕儿了。真是不识好歹!可人家客户指名要他,也就只好忍了。接下来不说你也知道,稿费上去了,客户总认为是花大价钱请的爷,而且还真象大爷一样伺候着。再说了,人家老马的尊容加上表面看来随随便便实则精心配置的行头往那儿一坐。哈哈!怎么样?不服不行吧。
喜:是啊,人家马导确实有实力嘛。
彪:哟,南瓜饼来了,你也吃两块,这是我的最爱。小时候我家后院种不少南瓜,可我妈只会用水煮熟了吃。快,趁热。
喜:我不喜欢吃甜的,我老家也种这玩艺儿,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的猪特爱吃南瓜。
彪:靠!你骂谁呢?
喜:不不不,我不是骂你,想起了随便说的。你继续说马导。
彪:打那以后,老马还真是来了状态。片子越拍越牛逼,架子也端得越来越有样子了。这叫良性循环。叶茂中说过一句最令我佩服的话,人家把你当专家,你就得象专家,哪怕是装出来的。否则你自己没面子老板也没面子。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乡镇企业家和私营老板,他们不怕花冤枉钱就怕丢面子。面子你知道吗?你去发廊打一炮可能只要一百快钱。但是在KTV就不一样了。几个小时下来你顶多只能摸一下小姐的奶子,要是摊上个太平公主,连这点欲望也会落空。对了,这方面你比我专业的。咪咪的胸就够大的,你小子艳福不浅。
喜:得,彪兄你就别拿我开涮了。
彪:开个玩笑。买单的时候除了酒水钱,小姐和妈咪的小费各三百,小妹和少爷各一百,有时候还要替客人付小费。这一圈付下来少说也要三四千。够操他妈一条街的发廊妹了。可是这不一样,打炮要的是里子,在KTV要的是面子。人家老马的本事就是不光自己爽足里子,还给客户撑够了面子。这就叫吃相好看,也叫双赢。
喜:咳,人各有命。母牛遍地都是,但不是每个逼都大。按我妈的说法,我压根儿就不该进城。大学没考上还一个劲儿地想当什么艺术家,头发长就是艺术家啦?你姥爷的姥爷还留辫子呢,还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种田?
彪:哈哈!你妈还真逗!
喜:我现在倒是觉得我妈说的有道理。这些年要是不出来瞎折腾,孩子都该上小学了。人说培养一个贵族要付出三代的努力。我算是哪一代呢?
彪:你这么想就不对了。为下一代着想是指那些有了下一代的人。你我这不还是单身嘛。你不会告诉我咪咪去年打胎是假的吧?
喜:你说的也对。她压根儿就没怀孕。她为以前的男人打过几次胎。轮到我就怀不上了。
彪:这话怎么讲?
喜:最后一次打胎把子宫刮破了,留下后遗症。也好,我自己都养不活,哪有钱养私生子啊。
彪:别灰心。人说没有女人好起步,有了老婆迈大步。咱们从头再来。
喜:难啦!我都过三十了。三十而立,我现在是除了鸡巴每天还能立一次,别的都软了。
彪:哈哈!鸡巴能立就说明还年轻。只要抓住机会,咸鱼也能翻身。
喜:对了,你说你上礼拜捡了一个钱包的。后来怎么样?
彪:咳!看我把话题绕的。咱们再来一瓶啤酒,我慢慢给你说。也别一瓶了。干脆叫一箱得了!喂,服务员,来一箱三德利!
喜:太多了吧,我不行的。
彪:男人千万不能说自己不行。今天高兴,我们尽情的喝个够。
喜:好!只要你高兴,我奉陪到底。
彪:不是我高兴,是我们都该高兴!
喜:好!
彪:干!
喜:后来那钱包——
彪:你又来了,这不是正想说嘛!
喜:我听着呢。
彪:其实三百块那天对我来说已经足够诱惑了。我本来打算去酒吧喝一杯然后走路回家的。有了三百块钱,我马上改了主意。我盘算着花一百块喝一杯洋酒,然后打车回我家楼下的那间发廊打一炮,剩下的钱再续张电话卡明天给老娘去个电话,告诉他老人家儿子在上海拍片很忙,年底一定会寄钱回家把盖房子借的钱还上。
喜:你也真是的,都什么时候了还撒谎。
彪:可怜天下父母心啦!寄钱的事我都说一百回了。她老人家比谁都明白。只要我在上海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我们家老爷子在我大学毕业那年死了,地里的活全靠老妈一个人干。我本来想回到老家文化馆上班的。可我妈死活也不让我回去。说上大学就是为了让我做城里人。回去就是对不起祖宗。
喜:咳——真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啊!
彪:我算是在上海落户了。可压根儿就没人把我当城里人。我女朋友,你见过的,就是那个舒婷,她们家人老嫌我是乡下人。逮机会就把我奚落一番。
喜:你也真是的,有女朋友还去嫖。你不是挺喜欢舒婷的吗。
彪:操!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我告诉你,这读过书的女人要坏起来比蛇蝎还毒。尤其是读过书的戏子!
喜:算了,咱不说这些不愉快的事,说钱包吧。
彪:好!说钱包。这钱包可是捡得及时啊。来,再开一瓶。
喜:我来我来。你接着说。
彪:倒满了倒满了,别悠着啊。
喜:来,干!
彪:干!我告诉你,捡了钱包后,没到衡山路我就下车了。我怕那钱是假的,就给了一张司机让他找零。
喜:不会假吧?
彪:怎么可能!那司机看我提前下车。把一百块钱对着灯照了又照,一脸的迷惑。我拿了他找的钱抬头就过了马路。
喜:是街道吧?
彪:对。你没事吧。在我们老家街道就是马路。
喜:是是,马路。
彪:记得当时我是在天平路下的车。我看见边上有家烟店,又拿了一张一百元的买了一包中南海。
喜;你以前不是抽中华吗?怎么改中南海了?
彪:你以为我是谁啊?中华是我这种人抽的吗?
不瞒你说,以前你看我抽中华那是壳子。里边一大半是别的烟。你没见我从不给人敬烟吗?我抽烟抽到只剩下过滤嘴,谁知道我抽的不是中华?
喜:你也真够累的。
彪:谁说不是!哈哈!你瞧,这中南海可真够缺德的,硬是把他妈的LOGO印在过滤嘴上。你装都装不了。
喜:那后来呢?
彪:我刚点上一支烟,就看到一男一女走到我跟前。
喜:不会是失主吧?
彪:哪能呢,操!那女的我认识。
.. 喜:谁呀?
彪:舒婷。
喜:靠!你就说是你女朋友不就结了吗,还卖什么关子啊。
彪:错!是前女友。
喜:好好好,前女友。你接着说。
彪:我当时一看是这婊子,抬头就想过马路。
喜:那又何必呢。
彪:她倒好,跟没事儿似的冲我喊道:是你呀,怎么,不认识我啦?我心想你丫烧成灰我也认得。好,算你会演。老子我导戏的还怕你演戏的不成?
喜:你怎么说?
彪:这时候我才认真看了一眼她身旁的男人。你知道,一般情况下,只要有女人在,我是不会注意男人的。但这次例外,他身边的女人是曾经被我全心全意操过三年多的前女友。
喜:看来你嫉妒了。
彪:放屁嘛你。我嫉妒他?我给你说说这逼的摸样,你都能把刚才吃下的鱼全吐了。
喜:有那么严重嘛?
彪:没等我开口,臭婊子又说话了:啊,我给你介绍,这是铿锵堂的朱总朱导演。
喜:哈哈!你不用说了,这人我认识。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彪:你认识?
喜:老兄,看来这两年你是走远了。他可算是个人物。我给朱导拍过片子。
彪:你说说这丫是什么来头。圈子里丑男人我见多了,黑馕够脏够丑吧?马良也胖,可人家够酷。我还真没见过象这丫猪样的。
喜:他的外号就叫猪头。个不高,体重是你我相加的和。地道的上海人,操一口地道的京腔,甭管春夏秋冬,一说话就出汗。这差不多是所有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他大学没毕业,原因不详。自称小时候是神童。七岁能倒背唐诗二百九十九首。其中杜牧的一首好象吹萧什么的他认为太色情,只记在心,从不吟诵。
彪:哈哈!你还真能掰。我想起来了,你说的那首诗应该是杜牧的《泊秦淮》,我也能背。“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喜:看来是够下流的。又是吹萧又是后庭的。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
彪:这说明你纯洁啊。那逼养的猪头确实够色情的。打小就深谙男女交媾之事。看来没少干坏事。
喜:早些时候听说他和黄辉一起干。拍些直销片什么的。黄辉你该认识的,就是东方电视台那个配音的。样子象太监,声音特棒。
彪:黄辉哪能不认识!我的那条卫生巾广告就是他配的音。记得当时他把凹槽念得象高潮,逗的客户直乐。差点还合作不成。
喜:客户不满意?
彪:客户嘛就是那臭德行。如果你不给他选择比较,再好的他都不满意。没辙,我只好把野芒叫来。可客户听了更不满意。说我这是卫生巾,是与幼嫩的肌肤相亲的产品。声音要有亲和力。不是豹子头林冲,更不是文化大革命呼口号。
喜:想不到一条卫生巾还真难伺候。再说了,卫生巾干吗非要男的配音啊。我看这个客户是变态。
彪:最可气的是客户最终还是觉得黄辉好。这不是难为我嘛。
喜:这下你可要破费了。
彪:我破什么费呀。客户自作自受自己认呗。我帮黄辉要了三千。周野芒九百。这些个爷我可不想得罪。上海的配音演员都抱成团儿了,说涨价就涨价。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你还就得认。得。咱不说这帮家伙了,说那个叫猪头的。
喜:后来他自己开了一间公司,就是你说的铿锵堂。刚开业就让人给坑了。好像还是安徽的什么池酒。听说那家厂子坑了不少人。你说这刚开张的小公司遇上这么个主。掉进他们的池子不淹死也得醉死。
彪:该死。真死了?
喜:那还有假?对外说是累了,不想干了。其实另有隐情。
彪:哦?来,咱们把各自手上的这瓶酒吹了。你继续说。
喜:朱导当时有个女朋友正闹着要出国。说是去汉堡。
彪:他们在一起多久了?
喜:具体不清楚,日子应该不短。
彪:这就对了。这么说吧。我以小人之心来猜测一下现实的背后。
喜:好。我倒要听听你能猜出什么道道来。
彪:咱们再开一瓶。
喜:还开啊?
彪:没事儿!大不了上厕所。你还怕把万科给淹了不成?
喜:行!谁怕谁啊。
彪:你看,这男人啊,就是不能胖。人一胖呢,很多不该大的器官就跟着大。而作为男人最重要的器官则正好相反。这我可不是瞎掰。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去洗桑拿。我可是亲自作过调查比较的。举凡胖子,不论高矮,他的鸡巴一定不大。有一回我跟一个台巴子灯光师去海阔天空,从冷水池子里上来的时候,我无意间看了一眼又矮有胖的台巴子,发现他的下身除了一撮黄毛,竟找不到老二!要不是去小便的时候看见他揪出那小螺蛳一样的鸡鸡,我还以为他是人妖呢。后来我发现,只要是胖子,都大同小异,这里边包括老外。
喜:靠!你丫真够流氓的。
彪:我也没说不是啊。还有更流氓的呢。于是我就纳闷,你说他们挺着个大肚子鸡巴又小,怎么做爱呢?十八般武艺我可是样样试过,就是想不出胖子的解决之道。
喜:难得你一片慈悲。可这也不关你什么事啊。瞎操心了吧。不见得人家胖子的老婆生孩子都是请别人下的种。再说了,说猪头就说猪头,你也犯不着打倒一大片呀。
彪:好在你不是胖子。要不然把你也圈进去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做爱的?
喜: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不是每个男人都和你一样瞎折腾。蹲着呗。
彪:哈哈!你牛逼!没错,肯定只有这一招了。你说现如今的女人哪,特别是城里的女人,早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大趴式。她们要解放,要翻身做主人。可偏偏遇上个胖子,才华是一回事,不能当饭吃。这样问题就来了。时间长了她就烦了厌了,最后就想辙跟你拜拜了。
喜:你是在说猪头吧。
彪:我说的没错吧?科学分析,有理有据。
喜:行了行了。要照你这么说,你女朋友也忒没眼光了吧。
彪:再纠正一次,是前女友。
喜:按说你前——女友舒婷也算是个大美人。该不会是有“蹲”癖吧。
彪:我呸!你丫说什么呢。别人我不知道,她我还不清楚。每次不把我折腾半死就不会甘休。
前二年我硬是被捆在一棵树上,眼巴巴瞅着满大街的美女徒伤悲。
喜:所以啊,她和猪头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彪:舒婷是谁啊,她可是个人精!你就等着看猪头将来怎么死吧。
喜:后来你们怎么收场的?
彪:我说了,听戏的搞不过唱戏的;演戏的碰上导戏的那还用问?
喜:你就吹吧。那钱包后来怎么样了?
彪:总算绕回来了。我一个人坐在酒吧里一边听着黑鬼唱歌一边掏出那钱包仔细看了一遍。发现那是个女人的钱包。
喜:有照片?
彪:幸亏没照片。要不然哪有今天!
喜:我不懂。
彪:人有时候就是怪。越是看不清的东西呢你越想弄明白。
喜:你发现什么了?
彪:几张信用卡。你知道我是不会对信用卡产生兴趣的。傻逼才会用自由去换现钞。
喜:你至少可以敲她一点现钞啊。
彪:弱智!再怎么穷,咱们也是穷艺术家嘛。你不这样认为吗?
喜:你是,我——不是。
彪:瞧你这点出息。没听马导演说吗?别人不把你当人,你得把自己当爷啊。
喜:我没见过你这样的爷。
彪:哈哈!今儿个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穷爷儿们。
喜:别兜了,说吧。
彪:我发现一张纸条。
喜:纸条?什么内容?
彪:内容可深了!
喜:不会是杀人的证据吧?
彪:当然不是,可性质差不多。
喜:那你快说。
彪:咱们一人再吹一瓶。我告诉你。
喜:你丫喝高了吧?
彪:什么话!我的酒有多深你还不清楚?
喜:那好吧。我今天算是被你套牢了。
彪:来了,干!
喜:不行,我得先上趟厕所。
彪:你小子终于憋不住了。
喜:厕所怎么走?
彪:服务员——给我们锅里加点汤,然后带这位先生去尿尿!
喜:靠!这儿的卫生间一点儿都不卫生!
彪:已经不错了。昨天我在茂名路的一间酒吧上厕所,那才叫脏!血淋淋的卫生巾就搭在坐便器上。墙上沾满了不知道是鼻涕还是精液的粘状物。我硬是把一泡尿给憋了回来。
喜:靠!你还让不让我吃了。
彪: 你什么时候变洁癖了?咱们可都是乡下人啊。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的马桶就搁在床边上。特大,不满不倒。
喜:你有完没完?我刚才看见熟人了。
彪:谁呀?
喜:王男。
彪:化妆王男?
喜:对。剃一大光头,手上脖子上还有耳朵上挂的全是藏珠子,挺酷的。跟一台巴子。就在后头窗户根儿那桌。
彪:她不是嫁老外了吗?
喜:嫁人就不能和别人吃饭啦?你有女人还嫖妓呢。
彪:哪个台巴子?
喜:李中诚。他们是老搭档了。早年上海滩拍广告的化装师就两个女的。还有一个叫林嘉。现在都是半老徐娘了。
彪:李中诚好像就住在万科吧?
喜:对。圈子里住万科的多了。人说住这儿的坐台小姐有多少,广告人就有多少。下半夜你拿大声公在这一喊,准能出来一个排的导演。
彪:这就奇怪了。这些人干吗爱这地方,路远不说,房价也不低呀。
喜:这你就老外了。早年上海像样的社区不多。二奶首选古北,艺术家喜欢万科。广告人都认为自己是艺术家。拍广告的自然就把这里当作香港的半山了。这是身份的象征。我和咪咪好的时候总想住过来,可她就是不愿离开仙霞路,说是她的小姐妹们都在那儿,串门方便。这下可好,我滚蛋了,她上班也方便了。
彪:哈哈!咪咪说的没错。仙霞路才是麦加。我正琢磨着搬到红灯区呢。
喜:你可得担心染上爱滋。到时候你就彻底在上海落户了。
彪:我谢你了。会嫖不算本事,有钱张子怡都愿意让你干。能嫖又会保护自己那才叫高手。我告诉你,作爱不带套是最危险的。没戴套,就是遇上仙女你也得忍了。你千万记住了,改改你的臭习惯。
喜:我一戴套就阳痿。所以除了咪咪我不和别的女人上床。
彪:天真!天真了不是。你是干净的,这方面你算是保持了咱们乡下人的高尚品德。可你怎么知道咪咪就不会背着你和别的男人上床?我告诉你,我和舒婷那么多年了,一次也没落下过。记得有一回我和她在达菲片场楼上老邱的办公室看黄片,看着看着来劲儿了就想干,当时没带套,可我想反正是自己的女人,漏个次把应该没事儿。扒了裤子就要上。你猜接下来怎么了?
喜:中弹了?
彪:什么话!舒婷不干了。
喜:这也正常,人家怕怀孕嘛。
彪:这是个好理由。一般情况下是成立的。可我是谁?她的月经周期我是一清二楚。那几天我就是拿杯子往里倒精液她也怀不了孕!她说她还是习惯我戴套。
喜:忍一回死不了人的。
彪:操!当时我满脑子都是电视画面上那个洋妞的肥臀大奶。我借口尿急上厕所硬是自己给解决了。
喜:你丫整个一公猪!
彪:嘿嘿,我不当你是在骂我。按说舒婷的性欲绝对比我强,平时我给个眼神她都会扑上来。可那天特冷静。这事儿一年后我才整明白她当时为什么不跟我干。
喜:为什么?
彪:她有了别的男人。
喜:她倒是够义气的。
彪:错!只有一种可能。她当心自己不干净,怕万一把我染上。
喜:恩,算有良心。
彪:我说你丫怎么就这么面?被人卖了你还帮着数钱!
喜:不是,我是说他还是关心你的。
彪:幸亏当时我没干。
喜:人家也没让干啊。
彪:咳咳!你干吗和我抬杠?
喜:好好好,你接着说。
彪:打那以后她再也没让我亲她下身。家里浴室的皂架上还多了一瓶怪味儿的洁尔阴。
喜:女人都用那玩艺儿。咪咪就一直用。
彪:那是你的女人。舒婷可不一样。我认识她那会儿,她还是一个处女。我敢说这一点上戏毕业的女生,她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可能杀了你都不信!
喜:不杀我也不信。
彪:在我眼中,她绝对是冰清玉洁。有时候我舔过她再吃饭都不带漱口的。你说这冷不丁儿的用起了什么洁尔阴,我能不纳闷吗?再说了,自打跟她好上,我和别的女人顶多是过过手瘾,绝不上床。不可能是我的原因。
喜:看来是红杏出墙了。
彪:喂,我注意到那边李中诚在隔着裤兜搔痒呢。已经好几回了。他以为隔着桌面光头女人看不见。哈哈,被我看见了。
喜:你丫积点德好不好?大老远的你往那儿看什么。
彪:嘿嘿,我估摸着李导的下身有问题。哎,那光头女人好像要走了。
喜:哦,我去打个招呼。
彪:你傻不傻啊,人家刚才碰上你已经够倒霉的了,你能不能识点趣儿?
喜:好,那我就装着没看见。
彪:好像李中诚也站起来了。没想到这老头儿艳福还不浅。
喜:你别瞎扯了。李导演胆再大也不敢在家门口泡妞啊。他老婆可不是省油的灯。奥菲丝就设在家里。主要的工作除了带孩子就是盯住老公。
彪:老婆?他有老婆吗?我还以为他是个孤老头呢。
喜:他可不老。人家刚过四十。
彪:操!我还以为他少说也有五十了呢。
喜:是长得成熟了点儿。后面新盖的优死美帝小区住一澳大利亚老外,也是导演,开始我以为他七十多了,一打听才五十出头。找一中国太太比他小二十岁。
彪:你是说比尔吧,我在北京就认识他。特爱泡吧。胡子长得好看。样子特象冯小刚电影《大腕》里的泰勒。我说,你坐直了,他们走了。来,吹一瓶。
喜:好哩。干!
彪:刚才说到哪儿了?
喜:说他象泰勒。
彪:我是说李中诚。
喜:噢。你别看他长得象高雄的渔民。几年前可风光了。
彪:对。我听说他也开过制作公司,后来倒了。
喜: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早年上海的广告导演四大金刚也叫四人帮他算一个。另外三个是富敏、俞缸还有李血颂。李血颂是个娘儿们。
彪:我知道。那骚娘儿们靠小日本的片子养着都快忘了自己是哪国人了。
喜:要说开公司我最佩服富敏,当年神兵怎么样不用我说。泡忸呢,俞师傅最本事,这丫最擅长吃窝边草。他公司里女人只要有几分姿色总逃不过他的魔爪。就连后期公司的女制片他都不放过。有一年还追到北京去泡。简直是到了不惜血本的地步。
彪:是啊,要不然开卖拉后来也不会濒临倒闭了。难怪他老婆要离婚。
喜:他老婆?一样!就象你说的,戏子无情。臭娘儿们咱就不说了。说到拍片,还是李中诚到位。当年一条三十秒的姚生记瓜子,硬是把三十年代的老上海拍活了。到现在也没人能超过他。
彪:哈哈!看来,你丫是装傻嘛。没有你不懂的。
喜:跟你比还是有距离的。
彪:我认识李中诚的时候他可是有小密的。用他的话说是助理。有意思。老板的小蜜叫秘书,导演的小蜜叫助理。摄影师的小蜜叫什么?
喜:叫坐台小姐。
彪:哈哈!你真能自嘲。
喜: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啊。
彪:什么意思?
喜: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年轻人起来了,老家伙们风光不再了。李中诚还算明智。先是灭了小蜜。再是关了公司,然后是把老家的黄脸婆和孩子接到大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专心拍片。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要不然现在的广告圈哪还有他老人家的一席之地啊!
彪:老的不死,新的不生。咱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喜:对了。这酒已经喝半箱了。你那钱包可还没下文啊。
彪:操!这不是你把话提绕开的嘛。怎么还倒打一耙?
喜:好好好,我错了我改。你接着说钱包。谁打岔谁是孙子。
彪:上回说到哪儿了?
喜:纸条。一张纸条。
彪:一个男人写的。两人关系还不一般。
喜:什么内容?
彪:只有几个字:最近勿访,家属在。
喜:这太一般了。一对普通的婚外恋人。
彪:内容简单,可签名和那张纸不一般。
喜:哦?不会是陈良雨吧?
彪:官没那么大。但也不小。
喜:谁啊?
彪:春澜公司的副总裁。
喜:张志强?
彪:对!就是他!
?
喜:操!原来是这个王八蛋。平时一副正人君子的摸样。我还以为他真的很正派呢。
彪:这就是你的可爱之处,也是你的致命弱点。人要学会相信事实而不要轻信外表。象张志强这种人绝不可以用好色这种低级的定位去衡量他道德。一个人要爬到他这样的职位单靠业绩是不够的。企业不是政府,搞个把形象工程就能升官。张志强靠的是手段。
喜:什么手段?
彪:要问张志强这些年在春澜集团的表现,那叫业绩平平。但在李总裁眼里,他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帅才。什么叫帅才?帅才就是人长得帅而且口才好的人才。这种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给春澜卖了多少台电器。而是在关键的时候能起到关键的作用。一般的企业家想到攻关只会想到美女。既然大家都能想到,说明漂亮的女人绝对是祸水。李总是战略家,当然与众不同。对张志强来说他算是遇到伯乐了。
喜:男女都一样,不就是美人计嘛!你丫别跟我说一大堆破道理了。我在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参加过他们的两次比稿,都给刷了下来。不过那丫还算有点人性,每次都给落选的公司一万块钱比稿费。
彪:这就是手段。回头我再说比稿的事。你听我把刚才的话说完。
喜:行啊。先喝口酒吧,别干了嗓子。给我棵烟。
彪:中南海行吗?
喜:行。对我来说能点着的就是好烟。对女人也一样,只要有奶子,长什么样无所谓。
彪:哈哈!想开了就好。别一根筋挺着,累的是自己。
喜:接着说。
彪:你去过春澜公司总部对吧。
喜:当然去过!第一次我还有点怵,以为走错门了。一般的国内大公司门口都挺花哨的。可他们公司外面一溜的大理石高墙还架着电网红外线,都快赶上美国领事馆了。要不是铁门边挂着块铜牌,我就得在南京西路来回拉锯了。
彪:说的没错。就是这幢大洋房奠定了张志强在春澜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喜:这房子是张家的?
彪:怎么可能!他张志强的背景和你我一样,三代贫农。只不过多了一张华师大的进修硕士文凭。
喜:学什么专业的?
彪:什么专业都不是的企业管理。那年月搞一张象他那样的文凭就象在生产队开介绍信一样容易。
喜:我看这家企业有毛病,在江苏那么牛逼,厂区都赶上我老家的县城了。非得把总部迁到上海这人挤人的地方。
彪:这你就不懂了。上海是什么地方?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国际大都市。一个企业在上海占有一席之地就意味着站在国际市场的前沿。这种象征意义李老板可是清楚的很。浦东那些高楼他是没有兴趣的。他早就看上南京路上的几幢洋楼。可一打听,全是文物,一句话,人家不卖!所以啊,这件事就落到张志强手上了。
喜:靠!他张志强有那么大能耐?
彪:长话短说吧。当时分管招商口的副市长是个刚刚提拔的年轻干部。新官上任,铁面无私。张志强拿他是没辙了。这时候他听说这个副市长是市委副书记米雅琴的老部下。心里就有底了。米雅琴是个女的。
喜:一个过了更年期的老女人,不会对帅哥感兴趣的。
彪:错!这米雅琴可是个丰韵犹存的寡妇。什么叫丰韵犹存?说白了就是性欲犹存。早年他不过是部队的一名宣传干事。因为长得漂亮,没少让首长门卡油。后来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师政委。专业后在地方也和部队一样,尽被那些老头子占便宜。好处是不断升官,一直做到现在的位置,算是她这一生付出的回报。
喜:靠!破鞋也能升官。
彪:我告诉你,玩女人可能要丢官,但被玩的女人就一定有机会升职。
喜:什么世道!
彪:这叫改革开放的世道啊!两年前,老头子死了。她倒是焕发了青春。
喜:你别逗我了。哪个官儿会对老太婆有兴趣。她以为自己是宋祖英啊。瞎子点灯,白费蜡嘛。
彪:没人对她的的身体有兴趣不等于他对别人的身体不感兴趣啊。你想,年青的时侯总是被自己不喜欢的人干,那是没办法。就象坐台小姐,时不时的总要去找鸭子平衡一下心理。我敢肯定咪咪以前也干过。
喜:你能不能举别的例子啊。不过,冲她有权我倒是原意牺牲一次,可我怕面对那堆皱巴巴的囊肉,直都直不起来。
彪:你还没那福气!张志强听说米副书记喜欢晨跑,就在东湖宾馆开了间房,每天早上都穿着短裤背心到武康路锻炼。
喜:这小子够聪明!
彪:张志强的模样就象当年台湾政坛上的小马哥,属于典型的师奶杀手。他和米副书记搭上关系后就分不清谁占谁的便宜了。用米副书记的话说,春澜集团总部进上海那是对上海有利的好事。所以张志强后来成为那幢大洋房的实际主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当然,更多的时候他必须在武康路的另一幢小洋房过夜。
喜:那他老婆呢?
彪:他当然有老婆。凭张志强的条件,他完全可以找一个才貌双全的女人结婚。可是,当他以恋爱的名义尝过各种美女的味道后,最终决定在太州老家娶一个和他有着同样家庭背景的普通小学老师为妻。在他看来,女人一旦结了婚,身份就变的很简单了,就是终身保姆。令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家的保姆还是有文化的。绝不会干出伤天害理得事。
喜:这丫够黑的。自己一条烂肠子,在外头干尽坏事儿,还要让一个良家妇女为他守活寡。我要是他们那儿的人,一准找机会教他老婆享受通奸的快活。
彪:你就歇着吧。好了,时代背景交代完了,我得告诉你另一个人的身份了。
喜:对对对。你还没说钱包的主人是谁呢。
彪:娇点传播的女老板许丽。
喜:我靠!这世界也太他妈的小了!
彪:怎么,你和她有一腿?
喜:那哪能呢,我两次到春澜比稿都碰上这臭娘们。真他妈倒八辈子大霉了。原来张志强这王八蛋在演戏啊。我整个一傻逼!回来还一个劲儿的改创意。操他个祖宗十八代!
彪:祖宗就别操了。将来操他女儿吧。
喜:哎,你怎么知道那钱包就是许丽的。
彪:哈哈!你不服我还不行,这就是我阿彪的过人之处!
喜:对对。你以前也就是运气还差那么一点儿。能力是绝对没问题的。
彪:虽然你这句话恭维的成分很大,但基本符合事实。我就笑纳了。
喜:那你接着说。
彪:当时我一看那张纸特眼熟。酒吧里的灯太暗,我就拿打火机点着了仔细看。
喜;对了,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张志强写的条?
彪:用同样的纸写的条我家里也有一张。
喜:是写给舒婷的吧?
彪:这回你丫脑子不笨了!
喜:还是的,咳,这世界太小了!
彪:你想,要不是碰上张志强这等高手,舒婷怎么会背叛我呢。
喜:他们俩怎么会认识的?
彪:要说这个,那还是我的错。去年春澜集团在报纸上登广告要选什么形象小姐。是我鼓动舒婷参加的。
喜:我明白了。形象小姐没选上,大款却傍上了。给舒婷的条子写的是什么?
彪:也是几个字:必须打掉!
喜:***!逼人打胎啊。
彪:从那以后,我和舒婷就彻底分手了。天平路那次是分手以后第一次遇上。
喜:你还是说怎么知道许丽的吧。
彪:按说除了那张纸条,钱包里也没留名片或照片什么的,我阿彪就是福尔摩斯再世也知不道钱包的主人。就算有照片,就许丽那母夜叉,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把人民币抽出来然后把钱包扔进厕所。
喜:呵!来,为你的缺德干一瓶!
彪:什么话!象许丽这种女人,除非她分一半股份给我,要不然打死我也不会跟她上床。
喜:你就做梦吧。快喝了!
彪:你还真说对了。这梦啊,就快要实现了。不过不算多,也用不着跟母夜叉睡觉。
喜:你就别绕弯子了。
彪:当我确定写条的人就是张志强的时候,马上就用吧台的电话找到了可能还在和猪头吃饭的舒婷。
喜:你问她?亏你想得出来!
彪:当然要问她,也只有问她!
喜:有戏!接着说。
彪:我开门见山。直接告诉她我这有一张张志强写给女人的纸条。
喜:她什么反应?
彪:她说阿彪你够可怜的。操!那意思就好象我的新女朋友又落在张志强手里似的。我说谢谢您了。目前我阿彪正在治疗心灵的创伤,暂时还没考虑找女人报仇。
喜:哈哈!你有种!
彪:她听我这么说,也不问原因就撂下一句话:娇点传播的许丽。
喜:一日夫妻百日恩哪!
彪:你丫什么意思?
喜:有意思!
彪:你看,那边又来熟人了。这里还真是牛鬼蛇神聚集的地方。
喜:富敏的面子还是够大的。不过这里的鱼也不错。那个胖的是远东,戴眼睛的瘦高个是谁我不认识。
彪:俩儿我都认得。另一个是毛德凉。
喜:名字耳熟。
彪:老毛原来是呻吟策划的老总。后来把公司交给杨嵩了。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喜:好像有两年多没声了吧。
彪:对。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出国热那几年,去澳大利亚洗过盘子。回来硬说是liu si遭迫害才出去的。操!遭迫害他还回得来吗?号称自己是策划高手,可自从我看过他写的东西后,复旦大学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就彻底倒了!
喜:没那么严重吧?
彪:你看他给你留下第一印象什么样?
喜:怎么说呢,年龄不到五十,挺儒雅的。
彪:操!这丫就靠他的虚假外表骗女人。其实他四十还不到,比远东大不了多少。他是个老狐狸。
喜:这么了解,你跟他合作过?
彪:我能跟这种傻逼合作吗?我一哥儿们的表妹是这丫的小蜜。报社编辑,三十多了,加上坏一只眼,老毛要是甩手,估计她也就没活路了。
喜:看来小蜜也是靠不住的。什么时候把你卖了都不知道。
彪:如果你只有一个小蜜并且对她好,通常是不会出卖你的。
喜:他有很多女人?看不出来。
彪:头几年就连他老婆都没发觉。可他就是能耐,同时和三个女人周旋,俞师傅都佩服他。
喜:对了,我听说他和俞缸还合作过。
彪:没错。早期他们一起开公司。没多久就分了。我估计多半也是为了女人。远东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跟毛德凉的。可以说没有老毛就没有远东的今天。
喜:噢,还有这么一说。新鲜!
彪:你和远东合作过?
喜:算吧。神兵的一个小专题。他自己没来。找了个助理监督我们干。
彪:远东在圈内也算是把老刀。早期做制片的除了老邱和上影厂的几个人,端得出的就数他了。
喜:他不是老毛带出来的吗?
彪:老毛充其量只是领他进门。这丫在我们学校学的是表演。后来分配在剧团。要说演戏,你都比他强。当制片还算块料。
喜:他演厨师挺合适的。
彪:错!最好的大厨演员是马良!
喜:对对,我想起来了,马良演过大厨的。
彪:说实话,远东自己从来就没想过会成为专业制片。
喜:他想演戏?
彪:想当导演。
喜:那他为什么不做?
彪:做过。
喜:拍过什么片?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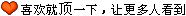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