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夜里,维戈没有原由地从梦中醒来,外面安静极了,听不到一丝风声,只有自己和奥兰多的呼吸声在不大的空间里此起彼伏。水银色的月光从窗口投射进来,正好照在睡在地铺的奥兰多身上。维戈没有办法不去看那个沐浴在月光下修长美丽的身体,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白天在花树下,他凝望自己的双眸。几度辗转反侧,他开始烦躁起来,用被单蒙住了头,依然无法入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奥兰多的呼吸变得沉重了,嘴里不断急促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维戈犹豫了一下,还是翻身下床,轻轻拿开了年轻人搭在胸口上的手臂。刚要转身时,奥兰多猛然间大喊了一声坐起了身,维戈没有一点防备,被吓了一跳。
“奥兰多?”稳下心神后,维戈试探地拍拍他的肩头。后者没有任何的反应,直直地看着前方,眼神空洞洞的,胸口剧烈起伏,显然还处在刚才的梦境中。维戈举起手在他面前晃了晃:“你没事吧?”
年轻人连续吞咽了好几下,侧头看看维戈,眨眨眼睛,长出了一口气:“我没事,只是做了个可怕的梦。”说完他擦擦额头的冷汗,紧搂着自己的外套靠着墙上,闭上眼睛,呼吸渐渐平缓下来:“刚才,我梦见妈妈了。”
维戈借着月光燃起蜡烛点,倒了一杯水递过去:“你每天都想着要和她见面,梦见她很正常。如果不是我的话,你现在已经在法国了和她相聚了。”
奥兰多捧着水杯呆坐着,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好半天后才一口气喝下去,把慢慢杯子还给维戈:“你不用这么内疚。我那天不小心把你给我的水搞丢了,又不敢喝别处的水,别无选择下才返回的,并不是有意要回来救你。而且,”说到这里,奥兰多咬住嘴唇,似乎在下一个很大的决心:“而且,我从一开始就在骗你,我去法国,根本不是去看妈妈,因为……因为在一个月以前,她就死了。”
维戈站在那里,局促地把杯子放下又拿起,略显生硬地说:“你去法国见谁,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之间,不存在什么欺骗。”
奥兰多瞥了他一眼,飞快地抓起自己的长靴套上,语气也冷淡下来:“我必须得走了,不能再留在这里。”
“现在?”
没有人给维戈答案,年轻人像是什么也没听到,捡起外套,坚决地拉开门走了。维戈跟出去,看着他急匆匆走过门前的空地,走过开满白花的栗树,在他跨进麦田时叫住了他:“你等等。”
奥兰多停了下来。维戈慢慢走过去,语气柔和低沉:“我知道我已经没有理由再阻拦你,但起码应该等到天亮,这个时候上路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甚至怀疑。如果是刚才我的态度刺伤了你的话,我……道歉。”维戈说着说着就变得有些结巴:“……我独自生活的时间太久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才能给你安慰。”
好像忽然之间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奥兰多的双肩一下垮了下来,手里的外套也滑落在地,随即他无力地坐在田垄上。看着年轻人哀伤的背影,维戈的心紧了紧,挨着他坐下:“有的事情,大概说出来能舒服一点。”
奥兰多抬头望着天上的明月,深色的眼眸里有些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你无需向我道歉。其实你一直说的都很对,你那天说,我是个胆小鬼,事实也是如此,即便是天亮了,我也没有勇气独自上路,我怕那些宪兵,怕被他们抓进监狱。”
“那天我只是……”
“不,我就是个胆小鬼,从小就是。”奥兰多猝然打断维戈的话:“小时候父母每次吵架,我都会藏到床底下,吓得发抖;到了都灵,那些大一些的男孩子欺负我,我从来没有还过手;十六岁了还躲在妈妈怀里无助的哭泣。”泪水终于冲破了眼眶,在奥兰多脸庞悄悄滑落:“一个多月前,宪兵抓走妈妈,说她是烧炭党人的时候,我不敢阻拦他们,甚至不敢去监狱看望她。直到知道他们判了她死刑,我才鼓起勇气去了,可看到她被折磨的……”
奥兰多哽咽着不再说下去。维戈缓缓将他拉进怀里,紧紧搂着,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安慰方式。月光下,白色的花瓣无风自落,轻轻洒落在他们身后,这样的夜晚,不知有多少花朵在静静地绽放,又有多少在无声地飘落。
回到卧室各自睡下好半天了,维戈的脑海中还不断回响着刚才奥兰多的那些话。月光的渐渐淡出了这间卧室,房间里陷入了一片黑暗。
“明天,我就和你一起去法国。”维戈轻声说,他知道年轻人和他一样,根本无法入睡。
“可你的麦子还没有收完。”
“事情总要有轻重缓急。”
奥兰多在那边沉默了一阵:“不能那样。妈妈说过,农民的所有指望就在每年的收获季节。你的病还没完全复原,我应该先留下帮你。等麦子收完了,我们再去法国。反正妈妈嘱咐让我办的事情我已经耽搁了这么久,再拖几天也没什么。”
“也好。”维戈无法拒绝年轻人的提议。在他的内心深处,或许正希望如此。
“你是用什么方法医好了我的病?你也是医生?”过了一会儿维戈又忍不住问起来,这有些不可思议,他从来没有这么好奇过。
奥兰多打了两个呵欠:“我曾经学过一个阶段的医学,因为不敢上解剖课,最终还是放弃了。在学校的图书馆,我无意在一本英国人写的医书上看到,生活在印度的人就是将烈性酒烧热,在病人身上反复摩擦,治疗瘟疫,至于效果如何,书里并没有说。那天我回到这里,看到你倒在树下……”年轻人的话没说完声音就逐渐小了下去,最后只剩下均匀的呼吸声。维戈也只能闭上眼睛,没过多久,他也进入了梦乡。
麦收进行的很顺利,三天后维戈家的房前屋后全部都晒满了脱粒过的麦子。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维戈今年的收成真的可以说是颗粒归仓。当然,如果没有那场暴雨,维戈和奥兰多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永远纯洁下去,不会有质的改变。如果没有……前面已经提过,已经发生的事情即为历史,历史是不可能改变的。
那场暴雨来得没有任何预兆。大半天的时间里,天空一直是万里无云。他们在栗树下打了个盹的功夫,浓重的阴云便布满了天空。两声炸雷后,暴雨倾盆而下,等把最后一袋麦子放进储藏室,他们浑身上下已被浇了个透湿。
维戈顾不上去脱下湿衣服,先在衣柜里给奥兰多找了一身干净的衣裤。在客厅,奥兰多已脱下了湿答答的衬衣,坐在他们平时吃饭的桌子旁,笨拙地给自己包扎伤口。维戈心里一阵内疚,这几天来,奥兰多不是照顾生病的自己,就是帮着干农活,晚上还睡在冰凉的地铺上,这些事让他忘了奥兰多手臂上还有伤。他拿过一条干净毛巾,默默走过去,接过奥兰多手里的绷带,细心地给他包扎好,并用毛巾轻轻拭擦掉他身上的雨水。两人的距离如此接近,以至于维戈能感觉到年轻人温热的呼吸荡在自己脸庞上,甚至能感受到对方的身体因为淋雨而散发出来的凉气,他的眼睛紧盯着年轻人裸露着的、结实的胸膛,一股灼热不可抑止地涌向下身,喉咙里不时发出几声奇异的响声。抬手抚上年轻人的脸颊时,两人的目光相遇了,维戈确认在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他渴望看到的情感和欲望,他慢慢抬起奥兰多的下颌,低头吻下去。两人双唇相触的瞬间,维戈身上那股燥热就以燎原之势燃烧起来,迫使他加重了吸吮的力度。一阵闷雷滚过他们头顶,奥兰多猛然惊醒,用力推开了维戈,站起来想离开却被桌子绊倒。他慌乱地站起身,抓过维戈拿来的衬衣,套在身上:“不,别这样,我不是,不是你认为的那种人。”
“是吗?那你告诉我你是那种人?十六岁那年又是为了什么事情躲在你妈妈怀里哭泣?”维戈喘着粗气反问。奥兰多脸色绯红,胸口剧烈地起伏不定,不再后退反倒扬起下颚看着维戈:“你总是这样吗?说话如此直接?我……”
维戈不再给他说下去的机会,不由分说地覆盖住了他的双唇,一只手搂住他的脖颈,另一只手不安分地摸下去,隔着潮湿冰凉的裤子,揉搓着那已经高昂的欲望。奥兰多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喊出来,但维戈不断用舌头肆无忌惮地侵犯着他的敏感点,最终他战栗着放弃了抵抗,任维戈褪去了身上的衣服。窗外雨越下越大,室内急促的喘息和压抑的呻吟几乎全部隐没在狂乱的风雨中。
第二天太阳升的老高了维戈才起床,这在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他不忍心去打扰还在熟睡中的奥兰多,一个人悄悄来到了储藏室,把昨天淋湿的麦子晾到了房顶。经过昨天暴雨的洗礼,天空更加的纯净蔚蓝。栗树花瓣在风雨中飘落了大半,嫩绿的树叶在阳光下焕发着勃勃生机。
晒完麦子,奥兰多还没有醒来,维戈上床趴在年轻人身上,揉揉他乱蓬蓬的头发:“懒虫,该起床了,都快中午了。”
奥兰多慵懒地睁开眼睛,连连打着哈欠:“你压着我,我怎么起来?而且,我感觉很不舒服。”
维戈连忙坐起来:“你哪里不舒服了?让我看看。”
“好像是头发和指甲。”
维戈又欺身将年轻人压在身下,这次年轻人似乎早有准备,先咬住了他的嘴唇,两个身体又纠缠在一起,直到都感觉饥肠辘辘了,才离开了凌乱不堪床铺。
去厨房前维戈体贴地问了一句:“早餐想吃点什么?”
奥兰多梳理好有些凌乱的头发,看看外面的天色:“应该是午餐才对。随便,我吃饭没那么大的挑剔,只要能吃饱就行。”
维戈不以为然地咧咧嘴,正要说什么,发觉奥兰多的脸色忽然变得不对劲,他回过头,宪兵队长卡维拉已出现在他家门口:“蒙坦森医生,有件事……他是谁,医生?”
宪兵队长眯起眼睛,警惕的目光在他们两人之间来回移动。维戈嚅嗫着,不知道该如果回答这个问题,几乎就在下一秒,有人将他大力推向宪兵队长,猝不及防下,他和卡维拉队长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下一刻,房间中那张桌子就压到了他们身上。维戈大脑中一片空白,几乎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是被人从桌子下面拽出来的。
“那家伙从窗口跑了,快去追。他跑不远,必要的时候就开枪,但不要命中要害!”
几名宪兵也从窗口追出去后,宪兵队长狼狈地整整自己的军装,咬牙切齿地看着维戈:“医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维戈咬着嘴唇一言不发。
“这下你麻烦大了。”宪兵队长不耐烦地挥挥手,上来两名宪兵用绳索将维戈紧紧捆住,并开始在他身上拳打脚踢。
一路上,身后的几名宪兵推推搡搡,维戈不断被他们掀倒在地又被粗鲁地硬拽起来。几天前就在这片田野边,维戈曾亲眼见证了宪兵们的暴行,想到也许每个垄边沟底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葬身之地,他就恐惧不已。还算走运,他被活着带到了镇上的宪兵队驻地,直接给推进了审讯室。
“说吧,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那个人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卡维拉队长脱下沉重的军服上衣,甩给手下,一屁股坐进椅子里。
“他只是告诉我,是去法国看望他的母亲,其余的什么也没告诉我。”维戈紧张地舔舔干涸的嘴唇。
“你的意思,你什么都不知道了?”
维戈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宪兵队长举起马鞭在桌子重重抽了一下,维戈吓得差点跳起来。
“去法国去看他母亲?你当我是白痴?那个女人上个月就被处以绞刑了。她顶着伯爵夫人的身份做掩护,到处进行不法活动,给那些叛乱分子提供资金,购买武器,发动武装叛乱。有一大批流亡分子就藏匿在阿尔卑斯山里,她儿子去法国一定是去投靠他们,想搞新的阴谋。本来他一直在我们的监视范围内,就是在你家附近才被他甩掉的。窝藏烧炭党人的后果是什么,你应该知道。现在,你还认为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可是,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维戈嗫嚅着。卡维拉队长提着马鞭走过来,凑到维戈面前:“医生,我的鞭子会让你想起什么也说不定呢。”
“不!”维戈惊恐地向后退缩,却被身后的宪兵挟制住了。
“再给你最后……”突然间卡维拉队长的脸色变得异样,很快他就捂着腹部倒在地上,全身抽搐。他的手下看到这些症状,明白是怎么回事,争先恐后地跑了出去。
“快解开我,如果你想活命的话。”这时维戈反倒冷静下来,背对着宪兵队长蹲了下去。
“我……不能那样。”卡维拉队长痛苦地蜷起身子。
“那你就躺在这里等死吧。”维戈近似冷酷地站起身后退了几步。
“别走,医生……救救我。”宪兵队长努力挣扎着站了起来,用身上的匕首割断了缚着维戈的绳索,随即他就支撑不住,摔倒在地,呼吸急促。维戈果断地割开队长的衬衣,冲着那几个朝门里张望的宪兵喊道:“快,生火。再去找酒,烈性酒,随便什么烈性酒都行!”
那几名宪兵不明就里地相互看看,然后四散跑开,很快就找来了维戈需要的东西,就在这间审讯室里燃起了火堆。
后半夜,牢房里又阴又冷,角落里几只胆大的老鼠开始活动,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维戈对这些都毫无反应,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般呆坐在墙角,事实上从昨天傍晚被关在这里后,他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动作。这期间,他曾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再去想那个人,却根本无济于事;也曾为那人的行为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企图让自己坦然一些,结果却更让他认识到了现实的残酷。一种被出卖和抛弃的屈辱感逐渐占据了他的内心,折磨着他已十分衰弱的神经,直到第一缕晨光照进牢房,他才缓缓闭上酸涩的双眼。
中午两名宪兵来到牢房将维戈带了出来。从阴暗的牢房来到户外,他的眼睛还适应不了正午刺眼的阳光,几乎被人推着上了一辆马车。行驶过程中维戈没有询问他会给带到哪里,是押送到监狱还是去绞死,似乎这些对他而言都无所谓了。行进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停在一片开阔地上,从窗口望出去,画着教会标记的白色帐篷一眼望不到头。带维戈来的宪兵打开车门:“医生,你到了。这才是你该来的地方,这个隔离区有很多病人,他们需要你。”
维戈动作迟缓地下了马车,面无表情地走向那片帐篷。
“医生,我们队长让我转告你,离政治那玩意远点,那真的会要你的小命。”
维戈身体僵了僵,停下脚步,再回过头来,那几名宪兵已驾车离开。
除了维戈以外,这个隔离区还有不少来自罗马和米兰的医生,但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每天玩命的工作。这些日子里,他不是累到极致绝不去休息,哪怕是短短的几分钟。日出日落,他就在这种麻木的状态下过了一天又一天,时间再次对他而言失去了意义。直到某一天,给他做助手的玛利亚修女实在忍无可忍了,连拉带拽地将他拖出了帐篷:“太不像话了,医生,你不能这样下去了,就算你想糟蹋你的身体也不该拉上我。你现在就去给我休息,立刻,否则我叫人把你绑在床上。如果你不信的话尽可以一试。”
维戈有些心虚地举手妥协,疲惫地靠着一棵大树坐下,连做了几个深呼吸。看他一副虚弱的样子,玛利亚修女不忍心再说什么,转身去给他准备午餐。午后的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照在维戈身上,倦意很快就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似乎他又在做梦了,又梦见了那个他永远也不想见到的人。半梦半醒中几匹快马从他面前的小路上飞驰而过,杂沓的马蹄声惊醒了他,他甩甩头,慢慢站起身,打算回自己的帐篷休息。这时那几个骑手又返了回来,其中一个跳下马背,走到维戈面前:“真的是你,医生,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卡维拉队长说着在自己脸上比划了一下:“我返回是想……哎,当面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及时治疗,我现在现在大概已经躺在墓地里了。”
“我是医生,救人是我的天职。”维戈勉强扯动一下嘴角:“而且,该说感谢的那个人是我才对。”
宪兵队长不解地皱皱眉,继而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你说那件事?你不必感谢我,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因为我们已经抓住了那个人,确切地说,是他来自首的。现在他已经被押解到都灵了,大概过不了多久……”
维戈脑子里一阵嗡嗡作响,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很快就淹没在一片黑雾之中,随后发生的了什么事情他就不知道了。再醒来时,他发觉自己躺在一辆行进的马车上,玛利亚修女陪着他。
“修女,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送你回家。维文医生说你身体太虚弱了,留在隔离区很容易被感染。幸好那几名宪兵知道你家在哪里,神父就让我跟着他们一起送你回家。”
维戈长叹一声,闭上眼睛,失去意识前的那段记忆逐渐苏醒,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他猛然坐起身:“请停下。”
马车刚停下维戈便跳下来:“队长,修女,不用再麻烦你们,这里已经离我家不远了,我自己可以回去。队长,烦劳你派人送一下修女吧。”
不等宪兵队长和修女有所反应,维戈便果断地转身走向田野,抄小路朝他家的方向走去。卡维拉队长和玛利亚修女面面相觑,没人能搞得清这个沉默的男人到底在想些什么。
家里还保持着维戈被宪兵带走时的样子,窗户大开着,桌子和长凳倒翻在地,到处落满了灰尘,一片狼藉。在镜子里 ,他看到一个满脸胡须,头发凌乱不堪,面无人色,双眼布满血丝的中年男人,无法相信那就是他自己。呆立了片刻他才醒悟过来,走进卧室打开衣柜,奥兰多那件外套依旧挂在那里。维戈双手有些颤抖地取下那件外套,紧紧搂在怀里,巨大的内疚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彻骨之痛压抑得他喘不上气来,脑海中回想着奥兰多说过那些话:“我怕那些宪兵,怕被他们抓进监狱……我鼓起勇气去看妈妈……可看到她被折磨的……”
窗外不时传来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抬眼望出去,那棵栗树上的白色花朵早已全部凋谢,翠绿的树叶迎风招展。收回目光时维戈的神情已变得坚定,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他仔细地把外套叠好,用一块干净布包裹起来,钻进储藏室,打开放麦子的箱子,将包裹深埋进去,又在箱盖上堆起一件件农具。随后他洗了个澡,刮掉脸上的胡须,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找到自己的火枪放进将要随身带着的包里,关好门窗,直奔镇上的宪兵队驻地。
“你打听这些做什么?”宪兵队长困惑地看着这个一小时前才和自己分开的中年男人。令他奇怪的不仅是对方提出的要求是那么的匪夷所思,而且此时这个男人看上去和一个小时前简直就是判若两人,难道仅仅是他刮掉胡子的缘故?
“我想去看看他。”中年男人的眼睛里都透着少有的镇定。
“医生,我不是让手下转告过你了吗,离政治远点。你是不是看你的麻烦还不够多?”
“那是我的事情,队长,你只要告诉我他被关在都灵的哪座监狱里就行了。”
宪兵队长的神情变得阴冷:“别忘了你在和谁讲话。依着我的脾气,该狠狠抽你一顿鞭子才能让你记住教训。好了,你走吧,别给人说过你来过这里,更不要再别人提及这个荒唐的念头,否则被关进都灵监狱里的人会是你。”
中年男人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宪兵队长恼火起来:“医生,你总是逼着我失去耐心。再不离开,我就让手下把你扔出去了。”
中年男人灰蓝色的眼睛里闪动着沉静的光芒,和上次在这里时的惊恐慌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毫不畏惧地向前走了两步,将自己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卡维拉队长恶狠狠地盯着他看了足足一分钟,最后还是败下阵来,避开对方的目光,拉过一张纸,抽出鹅毛笔写了几行字,说话的语气里带着些咬牙切齿:“我最讨厌欠别人人情。现在我们俩扯平了,下次我不会再对你客气。照这个地址,去找一个叫彼得的人,他是我老表,就在那个监狱做看守。哼,这不知是你运气太好,还是你倒霉的开端,谁知道呢,反正和我无关。拿去,立刻从我面前消失。”
都灵对维戈而言并不陌生,为了购买药品,他每年都要来这里好几次。按照卡维拉队长提供的地址,他很轻易就找到了那个叫彼得的人,那是一个蓄着大胡子,一脸诚恳的矮胖子。看完卡维拉队长的字条,上下打量了维戈几眼,认真思索了片刻,彼得挥挥胖手,让维戈回旅馆等消息。
又度过了一个难捱的不眠之夜后,第二天中午彼得就出现在维戈所在的旅店,拿出一身脏兮兮,还散发着霉味的看守服让维戈换上。看维戈犹豫不绝的样子,彼得扶了扶眼镜:“快点吧,不穿这个你根本别想混进去。要我说,你真够幸运的,要不是我们头今天去市政厅开会,你大概要等上十天半个月才有机会。”
维戈不再犹豫,迅速套上宽大的看守服。彼得又唠唠叨叨叮嘱了半天,这才带着维戈走街过巷,来到一个高大的城堡前。由于建成的年代久远,城堡的外墙被雨水冲刷的晦暗斑驳,厚重的石墙上嵌着一个个钉着铁条的小窗。高耸的塔楼上站着两名士兵,看了他们一眼就命令下面打开了铁门。
即使是夏日的中午,监狱的走廊里也是光线黯淡,到处弥漫着腥臭的潮湿气。听到某个角落里传出来一声声模糊的惨叫,维戈不禁打了个寒战,这个时候他竟然迟疑起来,自己真的做好了要去面对一切的心理准备吗?这个时候,走在前面的彼得停下了脚步,用钥匙打开一件囚室的铁门,冲着无声地维戈使了个眼色。维戈深深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踏进了那间囚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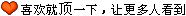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