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喜爱音乐,喜爱民谣的人们。音乐是始终能震撼心灵的东西,但震撼的音乐已经不多了,这个假期,我将在喧嚣的城市之下挖掘那些震撼的音乐,以此来获得心灵的慰藉...
此帖请勿转载,谢谢!
即便没有现代音乐工业,民谣依然会存在,只不过那最大可能是在我们的领域之外的,生长在城市里的人们或许终生都将无缘触及那样一种原生态的质朴、宁静与淡泊的和谐。唱片工业在批量生产民谣的同时也是在摧毁——无知觉的残酷的暴殄天物。在工业文明里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原初民谣精神赖以依存的环境的。随着田园时代的逐渐消亡,民谣于是险象环生。机器——强力的象征,它的行来碾碎了古老的田园,撕裂了一种古朴的声音符号。后来躺在现代危局里的民间乐器,像在迹近干涸的河床上的鱼,绝望地鼓动着腮帮。新的水流被灌注进来,但是其中充满了化学物,在之中延续生存着的鱼群中有一部分于是逐渐发现了产生于自体的残酷的变异,另有一部分归属灭亡。这也是民谣艰于呼吸的困境,被紧缚在庞大的唱片体制下的民谣,实际发出的是平静撕裂的哀歌。我们自此遭遇民谣的现代变异体:异教天启民谣、工业/死亡民谣、新民谣,甚至生拼硬凑的电声/城市民谣——把城市化的情感寄居于这样一种本来远离都市氛围的形式,这些都是诞生于现代的称呼和品种,或可以在形式上统称为“新”民谣。而真正的原生民谣并不向前一步,只是固执地隅居在民间天涯的一角,艰难地守卫、陪护着逼仄的在机械暴力下断裂残存的田园,亦较大程度上属于流浪乐人和忧伤的边缘的吟游者。
相对于原生态民谣的自之中变异而来的现代民谣不是意味着劣质品,但我也不认为它们是优化了的,仅是时代环境的不同决定着音乐自体的色彩。水生环境的恶化使当中部分过量吸收了化学元素的鱼畸变为食人鱼,与此相似,现代民谣具备了激进意识形态、阴暗感觉以及险峻的进攻性和暴力,触及,并深深地掘入了人类灵魂的阴暗。这是一个大的环境所致的,一种工业的、科技文明的环境,在其中,高贵的典雅风格抱紧冰冷的机械,提供了舒适的也供给出逸乐;充满希望的,也酿造出恐慌,那是在核阴影笼罩的地球肌体上遍布着的毁灭的新疫斑。道格拉斯从天象预测了地球末日,却没有预言到核武的人类末日,我曾经提到过,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次提出:军事核工业、人类在数量上的扩张、环境恶化与被无止境地贪婪劫夺过后的能源枯竭……这些对于人类来讲都太现实太客观!并且我发现“丰饶”这个形容词是只应该归属于田园和古老的田园时代的,它是一个充满了质朴感情的词汇。尽管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但现代人整体拥抱着的,以及环绕着现代人的那由工业所供给的并不是丰饶,“丰饶”只诞生于自给自足的纯粹的自然,而不屈从工业文明。在工业的天空下,及机械的怀抱中,属于现代的是看不见的血腥的积累及饱足的奢靡,而在两极分化的另一边则仍旧是流于边缘的困境,犯罪与恐怖主义由此滋生。于是原初民谣可以歌唱丰饶的质朴,而现代民谣却面临一无所有的贫瘠、寒冷与荒凉。从这里我们也许就能够多少了解到,为什么现在许多民谣乐队要向古代复归了。
民谣这种类型,当她尤其需要宁静氛围的时候,是很排斥都市和现代环境的浮躁与嘈杂的。从我们现在往回看已逝的岁月、遥远的古代,那肯定代表了一种深沉的寂静,在里面平和的心境和纯朴中不乏深邃的思绪适宜生成,自然培育成民间音乐的土壤。在中世纪民谣音乐里经常反映出古代映象,一种宁静或朴实的反照,作为现代人对实际上已经牺牲的古代环境的理想化追寻,同时也是对现代环境的绝望的背离。另有一些工业/死亡民谣团在音乐中也反映出对现代工业环境的绝望,但他们的作品却有直接对这种状况的或冷静或凶险的暴力的观照,他们并没有抛离工业环境而完全向古代回归;现代危局在他们的作品中成为一种重要题材,艰涩地隐喻化,悲叹朝向未来的破败。另外同等重要的是古代环境在一些类型的民谣里被反照的另一种形态。如果我们认为古代就仅是纯粹的平和与质朴,则将会被证明只是一厢情愿。底层民间中存在着的是质朴的生存性,但是在上层建筑那里则是向下的森严的王权和宗教压迫。当宫廷乐师在统治者阶层的大厅奏响华丽的乐章时,民间音乐在王权与教会的阴影下反映出了一种底层生存意志的质朴与苦痛,在这之中,既有屈从,也有反抗;既有淳朴的快乐,亦充满无尽的忧烦。而教会音乐在其外观化的崇高性与辉煌中隐藏着压抑感觉的阴森以及恐吓性质的麻醉效应,并不完全是牧师所宣称的光明圣境。对于教民及普通民众而言,存在于教会音乐里面的光明是具有一定的欺骗性的。那么在这样子的古老局面之前,民谣工作者们将会怎样有倾向性与选择性地去面对呢?——于是我们发现了发生在现代民谣里的微妙的分野:清新的悠远的质朴的与凶涩的荒凉的侵略性的;当然,在这分野之外也不乏共存的体验:共存,但无法交融,这种类型中作为特例的代表是邪异与古朴并置的The Moon Lay Hidden Beneath the Clouds。
初期布鲁斯可算是黑人民谣。现代乡谣展示了一种远离都市生活的洁净与清新。最大量采用古乐器,甚至直接按照古谱演奏的是中世纪民谣和一些启示录民谣,这样两种类型通常是最接近原初民谣的标准形态的。而民谣中的极端形态无疑当数工业/死亡民谣和部分新民谣,以及异教/启示录民谣,那些晦涩的难于予以理解的险恶元素正是来自这些民谣类型里的异端,它们在整体上的趋势是形成了对古代王权景象的复原,以及对基于反基督性上的异教权威的尊崇。现代合成器与采样机的运用为当中大量艰涩隐喻元素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各种声音在异常主题下的交融所形成的音响风景显示出了与往常相迥异的陌生感受:森严的,荒芜的,进攻性的,极度忧郁而痛楚的……民谣的可能性被改写,或可说成是达成了新途径的深开拓。
当我于某个深夜遭受到Death in June无边的绝望与孤独的侵袭而颤栗时,我曾认真地想过这种音乐确切地是一种暴力化祭仪极度抑郁的邪异观照,这种观照尖锐地撕裂了我曾以为够坚强的内在,把之掷回到遥远的血腥的荒凉,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孤寂绝境是在世界性的透明萧条之中的,而这还被我排斥掉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如果要细究意识形态,那我们与Douglas P势必是要彼此为敌的吧,那么有何种理由使我在Death in June的声音里感觉到对自我灵魂深切的抚触呢?拒斥与吸纳,都是处之险峻边缘。这种类型的音乐也许因为触及了人类共同的处境而撼动了我们,可能是现实性的,也可能是关于异教或时间性的。若都仅作为宇宙的穴居者在永恒黑暗里寻求一点微弱的光芒,生物之间将分不出差别。在天空中有太阳、月亮和星辰,也许什么都没有。一个宇宙,静止的,或旋转的,人在里面是什么?一个极微极微……的无方向的点,亦甚至不可能有形之界限。我发现,和在与无垠宇宙(时间)的相互静观里得到的孤独相比,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孤独要好受得多了;最黑暗的艺术经常能在这样的相互静观中诞生,对此我能想到的是Der Blutharsch观照古代的时间的雕塑群和Brendan Perry(Dead Can Dance)在嗓音里的悠远和荒凉。我最孤寂的时刻也就是这样,在模糊的幻觉里漂游时,突然发现自己是在宇宙的海洋里,这海洋是如此静谧与宽容,她在自己里面放置的物体同时也是在溶化的。若要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就不要把它置于宇宙之中,就不要妄图在想象中穿越宇宙。有时候我但愿更多地是生活中人,可以从现实里激发出一曲质朴的欢快的民谣来供给内心。至于异端民谣里最厉害的歌手,在我看来,要非David Tibet莫属。他可以展示最极致的忧郁、悲苦和在嗓音上尖利的极致变形,他也能进入到嘲讽式的淳朴之中。他的Current 93的异教性,大巴比伦沉沦的幻景,人类的未来仿佛在其中被焚毁。民谣的晦涩隐喻是在古代体系与现代危局里搭起的一座桥,这上面的良苦用心并不是预留给未来的永恒支出,在岁月的长久腐蚀下也不可能总是生效。也许在隐喻性的晦涩阴影中我们时不时想要回归到民间,追寻质朴的欣悦,而这就要涉及到一个原生态标准的问题,Ougenweide、Dead Can Dance、…The Soil Bleeds Black和Gor,以及另外一些,他们都在某些时刻曾经无限地接近过这个标准,但肯定地,在现在这个时代没有谁能完全达到这个标准,在未来也不会有。又或许,有一天你飞越过Gor式的五谷丰登,听到在青青野外,那古朴的,遒劲的,苍凉的一支歌谣,是草长莺飞的民间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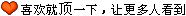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