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Kiss me, traitor!
作者:Osiris Brackhaus
配对:VO
级别:PG13
警告:angst
译者说明:
祝亲爱的dongdong生日快乐!
今年我至少可以骄傲地宣布:以下这个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在茫茫英文文海找到一篇二战VO,俺没有功劳也是有苦劳滴~)
但是你爱好的其他要素我就一个都无法保障了……
----
此刻,柏林帝国总理府宏大的大理石大厅内杳无人迹,皮靴踏在光亮地面上的刺耳声响在夜色中恐怖地回响。白色大理石柱与每面墙上无处不在的红色纳粹党旗形成了鲜明对照,元首的巨大青铜像透过空洞的双眼注视着夜色。
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经过这些走廊,最后一次穿过纳粹德国腐朽的心脏地带。这是他最后一次身穿可怖的褐色制服,虽然这身衣服很衬他。他已经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任务,现在他渴望回家,与父母重逢,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再不是罗兰·布卢姆,而是重新作为奥兰多·布鲁姆度过余生。
他刚敏捷地转过墙角,一只戴着黑色皮手套的手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进一根立柱后的阴影中。与此同时,另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捂住他的嘴,阻止了他可能发出的喊叫——如果他是那位招摇的开朗年轻的纳粹党卫军军官,他本该大喊大叫起来。
“嘘,罗兰,别出声!”一声低沉的耳语,奥兰多的心随之一沉,他认出那正是今夜他最不想面对的人。
他宁愿是撞见一整班持枪荷弹的党卫军预备队,宁愿是颠簸行进穿越雷区。这个男人威胁的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他的心。尽管如此,他依旧希望有机会毫发无损地逃脱,他点点头,捂住嘴的手松开了。
然而把他拉进黑暗中的双臂仍旧紧紧拥住他,想到不得不永远离开这样的怀抱,令他的心愈发下沉。
“维克托,”奥兰多低声说,“该死的你在搞什么?你想让我们俩都进监狱?”
突然间,他被转过身,年轻人望着男人的双眼。过去的几个月里,他违背自己的初衷,爱上了这个男人。依旧是笔挺的黑色制服,身穿盖世太保——纳粹秘密警察标志性的黑色皮大衣,维克托看起来完全是狡猾神秘的军官典范,自战争开始以来德国民众早已对他们心生畏惧。他们暗中监视每个人,哄骗人们揭发邻里、同事、亲人的任何“反德”行径。他们是国家机器隐秘而危险的中枢,其难以置信的根基令孩子们为了在“希特勒青年团”中获得晋升而出卖双亲。
然而他所了解的维克托全然不同,这是他从未敢想象的。
现在他双手捧着奥兰多的头,热情而近乎疯狂地吻他,将两人拉进角落更深的黑暗中。
不顾自己要尽早离开此地的意愿,不顾自己为两人着想要忘却与维克托恋爱的决心,奥兰多感觉自己融化在这个吻中,双手紧紧抓住他外套的柔软皮革,将他的身躯愈发拉近。
这个吻不只是愚蠢,简直是自取灭亡,然而此刻,一切何干。
他们的嘴近乎绝望地探寻彼此,亲吻噬咬,敏感的双唇蹭过因淡淡胡茬而粗砾的肌肤,两副身躯带着因绝望而生的疯狂激情紧贴着彼此。
绝望……?
奥兰多用力推开他一些,看着爱人。维克托在担心,他看得出来。不止于此,他的双眼如同暴风雨的大海般灰暗,有某种他以前未曾在爱人身上见过的神情。
“维克托,怎么了?”他急切地问道,不过仍然压低声音。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爱人低声说。
“怎么了?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们沉默地看着彼此,四目相对,双臂互拥,在对方的脸上寻找答案,却一无所获。
终于,维克托以一种令奥兰多冰冷彻骨的平平声调说:
“你怎么能像这样背叛我……”
他可能知道吗?他真的知道了?
可是他没有留下过蛛丝马迹,不可能知道他已经任盟军间谍多年。
上帝啊,有那么多考验,为什么你非要让我遇见维克托?我已经牺牲了我的自尊,为什么你还要伤透我的心?
感觉到心爱男人的身躯紧靠着自己,只有表明他们是体制精英的制服将他们分隔,不幸地,这个体制蔑视他们这样的爱情,奥兰多再次感觉到他所背负的这场恋爱远比他以前所自认的要多得多。他感觉精疲力竭,他厌倦了恐惧和没完没了的警觉。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另一种身份相遇?
“罗兰,回答我。为什么你要这样?”
维克托的声音虽然仍旧很轻,此刻却如刀锋般严厉刺骨,他的双眼如同他们身处的令人憎恶的宏大殿堂的大理石般冰冷。
“为什么啊,亲爱的?”
奥兰多尽力不看他,尽力摆脱他爱其胜过世间一切的男人的犀利目光,可是他无法说谎。至少这一次不行。显然他已经知道了某些事。
于是他强迫自己又抬起头,说话间他感觉热泪盈眶:
“我从来没想伤害你,我永远也不会伤害你。”他费力地说,他能看见爱人眼中的伤痛,那如同冰刃割过他的心。他近乎绝望地恳求:“我爱你,维克托……”
然而盖世太保长官只是默然地看着他,灰眸中满是伤痛与悲哀。而后,出乎意料的,维克托的神情镇定下来,他松开怀抱,干脆地说: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无意中听到一支搜查队已经被派往你的住所。一切都结束了。”是啊,显而易见。我的生命,连同我的爱也结束了。
“对不起,维克托……”
可他只是耸耸肩,拉平制服,完全置身世外的样子。
“如果我们抓紧,也许还能赶在他们封锁道路前离开柏林。”
我们?
“快点,我的车在外面。”
而后他转过身,示意奥兰多跟上他。他真的可以相信他吗?不过如果他想看着他被杀,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戏?奥兰多犹豫地一步一步跟上爱人,很快他又恢复了镇定,没有人会怀疑盖世太保长官和他年轻的副官在职业般的屏息沉默中离开帝国总理府有何异常。
----
“那么,我想现在是时候告别了。”一阵长久的沉默后,奥兰多说道。
有违意愿,这句话更像是提问而不是陈述,他看见维克托眼中的犹豫,那痛苦地证明:他们二人都宁愿自己不是现在的身份。站在柏林中央车站候车室的一角,在奥兰多登车离去前,他们还有一点私下相处的时间。他将去往相对安全的巴黎,在那里他可以求援。
年轻的间谍渴望最后一次抚摸爱人的面颊,以爱人的方式而不是他们伪装的同僚的方式告别。
突然间,砰砰的敲门声和刺耳的皮靴致敬声让他们转过了身,他们看见一位年轻的党卫军见习官走进房间,致以无处不在的敬礼:
“嗨希特勒!”他大声说道,他全身的制服和配饰如同新铸的硬币般光鲜亮丽。他对于他完美的雅利安党流苏上沾染的恐怖知道多少呢?奥兰多内心颤栗地想到。当我向其他人致意时,我是否看起来仍如此信仰坚定,细心的观察者是否能察觉我眼中的心计与恐惧?奥兰多思索着。
“莫藤森上尉吗?”见习官彬彬有礼地问道,长官略一点头,他继续说,“我得到命令通知您,将军的列车必须再次搜查,因为有消息说一个盟军叛徒在出逃。火车出发前,你们必须再等候半小时。将军为此次拖延致以歉意,请问您是否有何需要。”
无论维克托对旁人是如何说明的,显然他们接受了他的故事。不过另一方面来说,现在没人敢询问盖世太保的行动,唯恐怀疑他们的绝对正确会招致麻烦。
奥兰多想知道,这男孩看见了什么。两个受惊的情人在即将分离的黑暗一隅紧靠在一起?
也许不是。更可能的是,他只是看见一位高阶因而也异常危险的盖世太保长官站在黑暗的角落里,向人下达秘密交易和谋杀的指令。没什么特别的,不用看得太重。
男孩永远看不到在维克托外套褶皱下他们互牵的双手,也猜想不到二人在角落里寻觅的亲密远不及他们所渴望的程度。
“没有,”维克托厉声说,带着略微恼怒的语调,“如果我有需要会派人找你。”
见习官心领神会,又一个敬礼,答道:
“遵命,上尉。我相信您不想被打扰。到时候时我会敲门。”
维克托没有回应,只是不耐烦地看了男孩一眼,见习官小声告退,关上了身后的门。
奥兰多不得不忍住可怕的笑声。不知怎的,这情形非常滑稽。他们俩人都是令人畏惧又让人信任的组织成员,如同这座疯人院里任何人一样安全,然而他们却命悬一线。
还剩半小时。只有30分钟,就算拥有整个人生也许都不够。不知何故,奥兰多真希望那位见习官是来接他走,而不是来拖延又一段1800秒的痛苦。
“我……”奥兰多开口,徒劳地忍住涌上来的眼泪,“我有太多话想跟你说,维克托,太多话,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像是试图通过抚摸传达他的感情,奥兰多将手放在爱人胸口,不敢将任何感情迹象泄露在给予他们小小保护的外套外。
维克托仍旧戴着手套的手默默抬起,覆上年轻军官纤细的手,将它搁在心口,握住。
奥兰多能感觉到透过薄薄皮革的爱人手的热度,能感觉到维克托厚重黑制服下的心跳,他抬起双眼寻求爱人的目光。在那双眼中他看见太多的悲伤如大海般变幻而深沉。当他们有机会在床上一道醒来,在第一次清晨金灿灿的阳光下,他见过这双眼中的蔚蓝和喜悦;当他告诉他,知道他的背叛时,他见过这双眼中的灰暗与冰冷。
此刻眼中是如此多的悲伤,如此多的痛苦。还有爱。
“我不知道……”奥兰多低声说,不过戴着黑手套的一根手指将将碰到他的唇,维克托耳语道:
“那就什么都别说。那只会伤得更深。”
而后,仿佛那是世间最自然不过的事,盖世太保长官俯下头来吻他。
奥兰多一阵惶恐,苍白与灼热、冰冷与火烫同时袭来,他过分用力地推开爱人。
“别!”他挣扎道,却不知该呼喊还是该低语,他只得微弱叫道,“你在干什么,维克托?你会害死我们两个的!”
维克托再次靠近奥兰多,这一次把奥兰多逼进一个灰色大储物柜和墙角之间的阴暗中,维克托柔声说:
“罗兰,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明白的可是有点晚了,这话似乎该对我说。”
当然他是对的。众所周知,现在没理由害怕,没理由保护业已失去的。现在没有可畏惧的理由,然而如同刚刚奔跑过后一般,奥兰多的心在胸口撞击。
“我不是担心我的命,”奥兰多低声说,“只是担心你的命。”
朝年轻的党卫军官又走近一步,现在维克托终于把奥兰多逼到了储物柜后,一只手撑在年轻人脑袋边的墙上。
“叛徒,你什么时候关心起一个雅利安人的命了?”维克托一脸难以捉摸的神情。
这个指控比奥兰多预想的还要伤人。不过他早就知道事实是唯一的答案。
“从我爱上你的时候起,维克托。”
他的脸逼近奥兰多的面孔,维克托带着依旧难以解读的神情问道:
“为什么我该相信你,叛徒?”
奥兰多克制住想逃跑的冲动,因为他知道那根本没用。到底为什么维克托要让他经历这样的折磨?当维克托只想往他心头伤口撒盐时,为什么他还要假装要帮他逃脱?
“回答我!”盖世太保长官厉声说,依旧戴着手套的手握住奥兰多的下巴,扬起他的头,他不得不面对爱人刺骨的目光。“说啊,叛徒!”
“我爱你,”年轻的间谍哽咽低语,一滴眼泪滚落面颊。“我爱你,我永远也不可能伤害你。”
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事实,令他有勇气和信心抗拒自己的恐惧与混乱,他凝视着年长军官严厉的目光。慢慢地,他察觉维克托冷酷的控制动摇了,看见他面孔抽搐,他严厉的神情再次变成了悲伤和渴望。
“我知道。一直都知道。”维克托低声说,没有松开紧握奥兰多下巴的手,“你也许背叛了国家,可你从没有背叛你的心。”
他朝前俯身,他们的双唇堪堪将接,维克托用身体将奥兰多挤进角落,又说道:
“吻我,叛徒。”
这一次,他没有反抗。他对最后一吻渴望太多,他对也许来临的明天在乎太少。如果还有明天的话。
于是他回应了维克托的热吻,他吻他、抱他,仿佛永无明日。因恐惧和期盼而颤抖,他的手伸进维克托制服的外套下,难耐地拉扯他的衬衫,渴望触摸他的肌肤。
维克托没有反抗。丝毫没有。
奥兰多知道这不会止步于接吻,并非二人不渴望,可是他也知道,这纯粹是自取灭亡。每时每刻都可能有人走进来,或是透过窗户偷窥,或是在走廊里听见压抑的声响。
他知道,如果他们被鄙视,那他就该谢天谢地了。其他的可能是被送进监狱或是劳改营,送进某个无人生还的集中营。甚至被恼羞成怒的士兵用棍棒打死、用石头砸死也并非不可能。
过去一年里他所做的唯有一件事能让他有诸多丑陋的死法,他并不认为那是罪行,奥兰多自忖。
两人依旧站着,深深喘息,奥兰多后背抵着墙,维克托靠着他,一只手仍旧撑在年轻人脑袋边的墙上。
慢慢地,维克托的头垂到奥兰多肩膀上,他难以置信地听见他低声诉说:
“罗兰,无论你真名是什么,对于我的国家而言,你也许是个叛徒。可是就像你无法背叛自己的心,有些事我也无法做到。”
而后一个热吻,更像是在轻轻咬住爱人的脖颈,维克托又说道:
“我爱你,罗兰,我永远不会伤害你。所以我也变成了一个叛国者。现在你开心了吧?”
奥兰多依旧难以置信,神思混乱,他摇摇头。
“不,我不开心。我们身上还是有太多痛苦。”
一阵战栗,他停下话语。
“可是你爱我,”他重又找到呼吸,继续说道,“我配不上这样的馈赠。”
他颤抖着双手抓紧维克托的衣领,希望尽可能地稳住自己。
“还有我的名字,”他喘息着,眼睑半阖,“我叫奥兰多。”
“多美的名字。”
“奥兰多……”盖世太保长官在爱人耳边低语,“那意味着勇敢之人,忠诚之人。你的人民一定以你为荣。”
时间转瞬即逝,现实重又迫近,他们不发一言地分开。
“你没事吧?”维克托问道,他的双手重又隐藏进可怕的手套中。
奥兰多只是点点头,拂开爱人脸上垂下的一缕潮湿的头发,他神情悲伤依旧,却沉着平静,足以应对前方的险境。奥兰多发觉,维克托看起来甚至更放松了,简直比他们幽会时状态更佳。他如此完美,鲜明的轮廓配上文雅的高贵,只有一人能猜出他此刻并不轻松。
这是他想铭记爱人的样子,美丽而温柔。奥兰多暗下决心,他会将他永远铭记于心。
----
迈上几步台阶从站台进到车厢,奥兰多最后一次转过身,徒劳地希望能在拂晓的暗淡光线中看见爱人。然而站台空空荡荡,只有守卫加开列车的士兵,这趟列车是送一位德国将军和某些秘密货物去往巴黎。除了运送货物之外,帝国中央保安总局不信任空运,现在它将载着一位孤独的盟军间谍奔向自由。
或者至少是奔向比在柏林更易寻求支援的地方,奥兰多叹息地想到。
最后的告别迅速来临,令人惊讶的并无痛苦,年轻见习官敲敲门,走进奥兰多和维克托“等候”的房间。奥兰多忠于职守,作为上尉副官请求最后的命令,而后举手敬礼,转身跟随带他去车厢的见习官离开。
简单到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目光流连、含泪允诺。然而,奥兰多已经觉得自己想死他了。
不过而后他意识到维克托没有用相应的“嗨希特勒”回应他最后的敬礼,而是用通常的军礼“胜利万岁”。胜利万岁。
考虑到维克托已经知道他们是为截然不同的胜利而战,这让奥兰多疑惑哪一个才是爱人试图传达的可能含义。维克托不是一个会在这种状况下犯低级无谓错误的人。
不过在火车上他还有好多个钟头可做徒劳的沉思,奥兰多想到,他费力地转开目光,登上列车,一声刺耳的呼喊响彻站台:
“停下!停车!不准开车!”
强忍住惊叫跑掉的本能反应,奥兰多转身看向站台,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以防任何的风吹草动。
然而眼前的景象令他血液凝固:一队黑衣持枪的党卫军预备队跑下站台奔向列车,他们成群结队的出现通常只意味着一件事:盖世太保在追捕叛徒。
难道维克托出卖了他?难以置信。
是不是他的试图营救太晚了?也许他们已经追踪到了车站,现在维克托被控叛国,而奥兰多将要……
也许,也许根本什么事也没有,奥兰多想到。如果我现在逃跑,肯定被杀。所以我就坐在这,静静呆着,希望他们会找出旁人,放我走。
黑衣党卫军走近第一排士兵,他们的长官停下脚步,和最高军衔的士兵说起话来。他们离奥兰多太远了,听不见只言片语,然而这还是令他毛骨悚然。
很快,党卫军军官派出身边的一个士兵跑向列车前方报信。队伍慢慢散开,士兵和党卫军都站在站台上等候。
几分钟过去,毫无动静,奥兰多决定必须得做点什么以免自己陷入疯狂。
于是他走到列车门口,示意一个士兵过来。
“嘿,你,士兵!”奥兰多以最威严的口吻喊道,“过来!”
制服上的军衔允许他采用这种口吻,不出所料,那人走近列车。
“为什么耽搁了?”他满腹厌烦地问道,“我有重要文件必须送到巴黎,我没时间坐在这干等。”
士兵显然不知如何开口,不过最终还是谨慎地说:
“我不确定,长官。不过我听说,我们在等另一位乘客。”
“谢谢。你可以走了。”
另一位乘客?可会是谁呢?这趟列车是机密,是加车,维克托只是偶然知道这趟列车的存在,它去往巴黎的路上不会停站,也没有搜查。
不过至少不是因为他。可是他在这里多耽搁一刻就多一份被人发现的危险,会有人会派出另一支卫队,只不过这一次是为抓捕他。
他等待着。
他耐心地坐在座位上,试图阅读车厢里放着的报纸。可是奥兰多无法专注于文字,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却只能干等,他如何能坐得安稳。
他再也无法忍耐,又站起身,走向仍打开的车门。情况没有变化,只有光线更亮了,很快,第一缕阳光将攀上城市的屋顶。
奥兰多刚要再转身回到车厢,一个黑色身影出现在站台的暗处,身穿长长的皮大衣,拎着一个大旅行箱。
奥兰多心头一跳,他确信那是维克托正迈着稳健的大步走下站台,可是这不可能啊。可能吗?
奥兰多望穿双眼,视线模糊,他注视着那幻影,望着男人越走越近,依然极像维克托。
太痛苦了。
他愤怒到无语,看着男人与士兵和党卫军预备队说话,不知怎的,他仍然寄希望于这个男人会突然之间变成维克托以外的人。可是当男人转过身要迈步上车,要走进奥兰多正站着的车门时,他的模样还是没有改变。
“罗兰,”维克托高兴地说,“麻烦你接下箱子?抱歉我迟到了。”
奥兰多本能地接过伸向他的箱子,不过随后动作僵硬地朝前俯身低声说:
“见鬼你到底在干嘛?”
维克托微微歪过头,平静地回答:
“我和你一起走。”
简直是疯了!
“你不能为了我送命!你疯啦!”奥兰多低沉地嘶声说。
“我的命归我,我想给谁就给谁。我的心也一样。”
奥兰多摇摇头,徒劳地反对这愚蠢透顶的观点,又低声说:
“你他妈的疯了!”
“你要继续大吵大闹,我们就真他妈的要送命了。他们已经在盯着瞧了。”
突然之间,奥兰多又想起了周围环境,他努力笑笑,接过箱子。他友好地朝维克托伸出手,拉他上车,就像在帮助同僚,然而他们都明白,奥兰多接受了维克托的荒唐举动。
维克托身后的门一关上,就响起汽笛,列车启动了。奥兰多仍旧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地望着爱人,他看见爱人掸掸外套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说道:
“我觉得我会成为一位非常出色的间谍,你觉得呢?”
奥兰多沉默地摇摇头,只是盯着面前的深发男人,他如此华丽地证明:奥兰多对他还是知之甚少。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维克托厚脸皮地问,显然对自己的疯狂主意志得意满。
奥兰多又摇摇头,微笑着答道:
“我还能说什么呢?”
他走近爱人,把他拉到车厢门后,这样他们至少能有一些远离视线的时间,他抓住维克托的衣领,低声说:
“吻我吧,叛徒!”
The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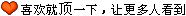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