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最后说一次,利加,你得等到我们午休时间。”奥兰多揶揄道,转回电脑前,盯着屏幕。
“得了吧!”伊利亚抱怨。
“伊利亚,你太使性子了。”丽芙咯咯笑着,拿着一摞文书走进里屋。“你在做新目录,奥利?”她狠狠瞪了伊利亚一眼。
伊利亚辩解:“他要做的,而且,是我在做所有的实际工作,他只是把它输入数据库。”
“我可以用电脑的,丽芙。”奥兰多轻声说,知道丽芙无论多么生气紧张、保护过度,都会原谅他的。丽芙只是叹口气,摇摇头,砰地一声把文件夹放在伊利亚旁边。
“你看,利加说最近你手的情况更糟了。”丽芙解释说,伊利亚呻吟着用手拍了下额头。
“利加!”奥兰多在屏幕后方怒视着伊利亚。“天啊,我不是让你去烦丽芙。”
“丽芙——”伊利亚把名字拖成了哀怨的长音,“我告诉过你不要提的。”
“瞧瞧,任性吧,”丽芙说,转向奥兰多,“他以为自己是老板,嗯?奥兰多,怎么样了?”
“丽芙,我发誓我很好,”他说,双手静止,“只是我这一个月挺艰苦,你们俩都知道的,不过现在大部分都好了,情况还不错。我甚至不用再包扎更长时间了。”
“奥兰多遇见了一个男孩,在地铁上。”伊利亚插嘴。
“你逗我吧!”丽芙惊叫起来,眼中流露出担心。她在奥兰多身边坐下,好奇地睁大眼睛。
“噢,拜托,干嘛这么吃惊?”奥兰多气鼓鼓地。
“奥兰多,你脸红了,”丽芙说,揉揉鼻子,咯咯笑起来,“噢我的天啊,利加,快看奥利的脸多红。”
“你们这些家伙……”
“好了,说吧,奥利。发生什么事了?”丽芙用一根指尖捅捅他的肩膀,问道。
伊利亚瞟了她一眼说:“他不会告诉你的,丽芙,现在你干嘛不去干实际工作?”
“我们今天成专业人员了?”丽芙挑起一边眉毛质问,“你觉得你能对我指手画脚,啊?”
“丽芙,我是你上司!”利加咬牙切齿,双臂抱胸。两人怒目相向,奥兰多小声笑起来。“这不好笑,奥利,我需要被认真对待。”利加皱着眉。
“等你脸上真正长毛,穿得不再像个小学生,不再像个色盲,不再像生活在八十年代中期,也许我们会的。”丽芙反唇相讥,奥兰多忍不住笑得更凶了。“现在嘛,不好意思,我和‘嗨,扭啊扭’(译者注:英文儿歌)还有十三个可怕的小鬼有约。”丽芙笑着说,从书架上抓起一本书得意洋洋地走向门口,伊利亚坐在那里直冒轻烟。
“我从来都没赢过她。”利加咬着手指说。
“那是因为你不可救药地被迷住了。”奥兰多傻笑着答道。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总是吵架,不过从没当真过。
“别提醒我,”利加呻吟着,“真难以忍受。”
“噢,对我你就别小题大做了,利加。来吧,我们早点儿开溜。”奥兰多提议,伊利亚立刻喜笑颜开。
“那你要告诉我你在地铁上碰到的那家伙的一切。”
奥兰多翻个白眼,拿起手套和外套。
“你说出来,午饭我请。”伊利亚提议。奥兰多想了想,套上了外套。
“好吧,不过我告诉你,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
“那么,让我搞搞清楚,”伊利亚戳着他的沙拉说,“这个随便的家伙在列车上接近你,问了你二十个问题,给你买了咖啡,然后还要你的电话号码?”
“差不多。”奥兰多吸着冰茶答道。
“奥兰多,作为一个以讲故事为职业的人……你真是一个糟糕的说书人。”伊利亚把一颗樱桃西红柿丢进嘴里。
“你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你了。”奥兰多反驳。侍者端着他们的午餐走过来,伊利亚示意要两个帐单。“少来,利加!我们说好的。”奥兰多极为孩子气地撅起了嘴,伊利亚差点被饮料呛着。
“真不敢相信你刚刚对我摆出这么幅面孔。我告诉过你永远都不要再对我做这种表情。”伊利亚咳嗽着说,“我不看,奥兰多。”伊利亚在椅子上转开身。“你还在做?”
“利加——”奥兰多拖长了音,眼睛睁大,目光阴沉。伊利亚皱着眉头面对奥兰多。
“你那样太gay了,奥利。你怎么能那样?那种……表情?”
“针对我妈的练习,不过我几乎没对她做过,”奥兰多微笑着回答,“现在,你是不是该付我的午饭?”
“给我点细节,我就付。噢,别再来奥利式噘嘴了,否则我的午饭要浪费了。”伊利亚指着一盘油炸食品对奥兰多威胁道。
“什么样的细节?”
“好吧,他看起来……什么样?嗯?”伊利亚倾过身子,等待着。
奥兰多想了想,吃着他的烤奶酪三明治。
“很职业。”奥兰多咬着嘴,坚决地说。
“还有……?”
“高个子,和我差不多。嗯,金发,带点红色的金色。有一点粗犷,不过很职业。”奥兰多可以在脑海中完美的勾勒出这个男人,温柔热情,嘴巴有点危险。
“是嘛,可他好看吗?”
奥兰多又瞪大了眼睛,他突然发现他的吸管很有趣。
“你又脸红了?奥利?噢天啊,你太……那上面没有字。看着我。”伊利亚坚持,奥兰多抬起了头,满面绯红。
“什么?”奥兰多小声问。
“你甚至还没说呢。”伊利亚有几分吃惊地说。非常明显奥兰多很害羞,源自于他保护自己的方式,他说话的习惯——没有自信,期待被肯定。伊利亚露齿一笑,一只手非常轻柔地放在奥兰多裹着绷带的手指上。“你知道你可以告诉我的。我觉得这件事挺棒的,也许你找到了值得结交……的人?”
“你在为难我,”奥兰多嘟囔着,垂下脑袋。“好吧,我觉得他很有魅力。”
“是对你,还是对所有人?”伊利亚问,享受着他让奥兰多局促不安的乐趣。他非常喜欢奥兰多,从他们大约四年前相识起,他还从没见过他的朋友这么害羞。
“准确的说,他不是那种英俊的好看——不过我觉得他算得上好看。我是说,好看并不足以准确合适的形容他。”奥兰多轻声说,甜蜜地微笑着。“他很美,你可以这么说。”伊利亚朝桌对面的奥兰多咧嘴笑笑,放开了他的手。
“他叫什么名字?”
“维戈。他跟我说,他是一个已康复的极端自我主义者。”奥兰多说,伊利亚哈哈大笑。
“哦?”
“但是他真的不是。我是说,我不这么认为。他很有趣,我……”奥兰多停顿了一下,皱起眉头。“我该怎么说?你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对我有那方面的兴趣?我是说,我不能问他,他也不能问我。‘嘿,你是弯的?’”奥兰多的笑容暗淡下来,他推开盘子。“我不该想太多。我只需要……给他打电话,然后再看情况。如果我真有勇气给他打的话。”
“如果他给了你他的号码,那显然他想要你打电话,奥利,”伊利亚一针见血,“现在,你还要不要吃那个了?”
奥兰多叹口气,在桌子下用膝盖顶顶伊利亚。“你请我吃饭,然后你吃了我的午餐。拿去吧。”伊利亚咧嘴一笑,把奥兰多的盘子拉到去。
“你得给他打电话,”伊利亚满嘴奶酪地说,“我的意思是,你总跟我说因为那什么,没有人正常看待你。好了,你已经找到会正常看待你的人了,没准还不止呢,你必须好好把握住,看看会怎么样。”
奥兰多消沉地摊在椅子里,戴上手套。
“那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
“我是说,我是等上几天,还是就……异性恋是怎么样的?”奥兰多问道,为伊利亚打开了冰箱。伊利亚弯下身,把打开的罐头放进冰箱,回头看着奥兰多。
“你说他有点疯狂,是吧?”
“是古怪,利加。他很……有趣。”奥兰多说,清空了门旁边的一个食品杂货袋。手指微微钩住塑料提手,他瑟缩了一下。“该死!我过去可以自己收拾杂货的,你知道的?”
“来吧奥利,让我来。”伊利亚站起来,从奥兰多手里接过袋子。“如果你今晚打,他也许不会认为你太急切。”伊利亚继续说,打开一些盒子,把它们放进了碗橱。伊利亚每月两次带奥兰多去购物,帮他拿袋子,然后打开一些稍后用得到而对奥兰多来说又很困难的东西。尽管奥兰多坚持他可以负担便宜的杂货送货服务,但伊利亚这样做已经一年了。
伊利亚打开一些猫食罐头,舀出来一些,肥猫在加热器旁熟睡着。
“难怪这儿这么冷。”伊利亚用靴子顶顶猫咪,那家伙勉强抬起脑袋。猫咪对着伊利亚一脸不爽,眯着眼睛,耷拉着耳朵,又回通风孔上睡去了。“我打赌这家伙一天比一天懒。他甚至都不嘘我了。懒鬼。”
“噢,别烦它。它是只可爱的猫,对不对,猫咪?”奥兰多温柔地说,小心地蹲下来,轻柔地抚摸猫咪的背。小家伙蜷起身,大声咕噜着,用脸蹭蹭奥兰多的手腕。“甜心猫咪。”
奥兰多轻轻拍拍猫咪,然后站起来,目光穿过房间盯着电话。电话应答机上的小红灯一闪一闪,奥兰多叹口气。“我有胆听吗?”他嘟囔着,伊利亚咯咯笑起来。
“别像个小孩儿似的。”伊利亚逗他,把一个蓝色冰格注满放进了冰箱。
“喂,我不是小孩儿,”奥兰多撅着嘴,大步走过房间,“你是不用应付她。”
“确实,不过她是个可爱的女人。”
“呃。”奥兰多呻吟着,按下按键,自我振作。应答机大声地哔哔响起来,读出了号码和来电时间。
“你好啊甜心,是妈妈。”索尼娅·布鲁姆愉快的声音传来,“你在吗,奥兰多?你今天下午在哪,嗯?你星期三不上班的,我只是讨厌想到你在给自己施加压力。现在我只是打电话核实一下,我知道你认为我这么做很愚蠢,可是我担心啊。你了解我的。”
“噢,老妈。”奥兰多叹口气,忍不住笑了。
“请给我回电话,让我知道你一直在吃维他命。你知道医生怎么说的。亲爱的,代我向亲爱的伊利亚问好。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两个不约会……不过……”
“什么?!”伊利亚尖叫起来,奥兰多红成了甜菜根。
“我妈妈她胡思乱想,”他解释说,尽可能快地按下了删除键,“她就见过你,噢,我什么也不知道!”
伊利亚也有点脸红了,拍着自己的额头。“看来我命中注定,永远都交不到女朋友。”伊利亚抱怨着,奥兰多勉强安慰地笑笑。“难怪丽芙总不给我机会,也许她认为……呸。”
“她只是瞧不起你,就是这样,”奥兰多说,一只手放到伊利亚肩上,满脸滑稽的笑容,“并不是说她认为你是同性恋。”
“噢,谢谢,我不存在的爱情生活到此为止。也许该明天打给他。”伊利亚决定了,把剩下的食品塞进冰箱。“你不必心虚,跟他在电话里解释一切,或许该等到你们遇上?”
“如果我们遇上,如果我打电话,都是如果,利加。”奥兰多说,在小厨房里坐下来,用脚趾脱掉鞋。这个举动不舒服,但是远远好过用手,也比穿着尼龙搭扣运动鞋到处走少些尴尬。“不告诉他,我会感觉自己几乎不诚实。我是说虽然他是没问,可我仍然这么觉得。”
“你用不着给自己贴标签,奥利。你不该总是想着它。”伊利亚柔声回答,坐在了小桌子的另一端。
“我有病,利加。”奥兰多叹口气。“最近,它总在我脑子里盘旋;我就是不能……让它停止。甚至现在,我做每件事都紧张,等着困难降临。我不知道现在没有你的帮助我能做什么。除非是冷冻快餐和花生酱三明治,不然我都没东西可吃。”
“我不认为你能打开花生酱盖子,我几乎都不能。”伊利亚怯怯地说。“事实是,这不代表你是谁。我所见到的远不止是一个EB病人(见文后译者注),一个患者,一个牺牲品。你独立,聪明,是一个好朋友。好啦,自尊心振作了没?”
奥兰多绽放笑容,踢掉了另一只鞋。“干得好。”奥兰多说,朝伊利亚温柔地笑笑。“想不想看点多愁善感的?”
“当然了,我正沉浸在放纵自己阴柔一面的情绪中。”伊利亚说笑道,奥兰多翻了个白眼。
译者注:
EB:Epidermolysis Bullosa Simplex的简称,也就是奥兰多所得的病,标准中文名译作“单纯大疱性表皮松解”(呃,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提了吧,汗……)。以后在文中提到此病基本都以EB简称。
EB:Epidermolysis Bullosa Simplex的简称,也就是奥兰多所得的病,标准中文名译作“单纯大疱性表皮松解”(呃,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提了吧,汗……)。以后在文中提到此病基本都以EB简称。
****
“你就说吧,伙计。”
维戈叹息着,把杯子放在了吧台上。
“我再最后说一次,肖恩,什么问题也没有。”维戈答道,叹息着转向他的朋友兼合伙人。
“我没说有问题,是你一整天都笑得像个十足的饭桶。”肖恩说,喝光了杯子里的剩酒,示意招待再来一杯。
“宾,今晚你真打算在这滥用职权?”那位可爱的澳洲招待问道,弯下身,把一杯冒着泡沫的啤酒当地一声放下。她朝肖恩调情地眨眨眼,用胳膊肘撑着自己,相当慷慨地露出了乳沟。令她沮丧的是,肖恩全神贯注于狂饮。
“我不会称这为滥用,米兰达。”维戈打断她,挖苦地笑笑。“我相信这该称之为暴饮暴食,至少圣经里是这么说的。”
肖恩哼了一声,放回酒杯。“今天以后,我需要一些……一打这个。”他摩挲着自己的额头说。
“噢,已经计划修改菜单了?”米兰达问,把一盘椒盐脆饼滑向宾。“慢慢来,宝贝。”
“对,这是属于我们的一年,我能感觉出来。”维戈靠进椅子里答道。
宾轻笑起来,脑袋搁在了吧台上,不住抱怨。“你年年都这么说,维戈。”
维戈微笑着摇摇头,“今年我想是了。”每年《纽约客》杂志都会举办一个寻找纽约全城15家顶级饭店和餐厅的活动,每年“公园广场的城市之光”居然都被遗漏在了名单外。
维戈不在乎这个活动所带来的地位或是宣传效果(他的餐厅不管在不在名单上都做得极好),他只是需要一些努力的方向,一些改善他自身和餐厅的途径。维戈就是这么生活的,从不满足,永远追寻更好。
他皱着眉,嚼着一块椒盐脆饼,脑子里琢磨着他的生活,而后决定他真的该再来一杯。
“请来杯苏格兰威士忌,米兰达。”他嘟囔着,双臂紧紧交叉在胸前。他从酒吧环顾餐厅,今晚这里坐满了富有的客人,笑意盈盈,相谈甚欢,享受着他们的晚餐。
为什么他还需要更多?
“苏格兰威士忌?”宾从吧台边站起来问道。“没错,今晚你明显有点不对劲,不是因为你要重新设计菜单。我们已经计划这个好几年了,而你把大部分工作都堆在我身上,你这个笨蛋。”
维戈咯咯笑着,晃动着米兰达放在他面前的酒。
“现在我……要去小便。”宾有点太过高声地宣布。吧台上一位衣着得体的女士生气了,吵闹着向烦人的同伴告辞。
“赶走客人了吧?我觉得你够可以了。”米兰达窃笑着说。宾稳住自己,威胁地瞪了米兰达一眼,摇摇晃晃地走向卫生间。
“到这个月底,他的肝好不了了。”维戈沉思地喝着酒。米兰达扬起一边眉毛,轻快地打开一瓶科罗那,滑向了吧台尽头的一位男士,然后又朝维戈走过来。
“那么老板,你到底怎么了?”米兰达诱惑地趴在吧台上问道,手上拿着扎着牙签的橄榄。
“拜托,米兰达,我们都知道这对我没用。”维戈说,从牙签上摘下橄榄丢进嘴里。
“但是……你找到某个能对你起作用的人了,啊?”
维戈张口结舌了半秒,而后咽下了橄榄。“你怎么——”
“看来你们总是忘记我是个女人。我们了解这种事。”米兰达撩了撩头发答道。
“我不认为肖恩忘了。”维戈反驳,试图想避开这个话题。“他只是今晚有一点情绪激动。我们正在重做菜单。”
“不用拼命讨我欢心,你可不喜欢这样。”米兰达咂咂嘴甜蜜地说。维戈向后靠进椅子里,发出一声短叹。“那么,是谁老让你笑得合不拢嘴?”
“我就不能……没来由的高兴?”
“你已经有一阵子没这样了。”米兰达支着脑袋说,“我记得最后一次,嗯,是你和那个犹太鞋匠约会的时候。”
“他是意大利人,是梅尔巴的厨师。”维戈摇了摇头说。
“我的记性太差了,不过至少我记得最重要的部分。你很快乐。”
维戈露齿一笑。“对,我是很快乐……直到那混蛋跟犹太鞋匠跑了。”
米兰达沉下脸,把她的牙签丢向维戈。
“你还是不打算说,呃?”她问道,从吧台上收起一些小费。
“我宁愿不要触霉头。”维戈笑着答道。“该死,差不多九点半了。我最好去找肖恩,把这笨蛋运回家,然后我再回家。”
“你确定不用叫出租车?”
“目前一杯可乐和一点苏格兰威士忌还不足以让我犯迷糊,不然我就真的要担心了。”维戈笑着说。“没有我,你们这些家伙关门没问题吧?”
“没问题,看看我们的工作,我想我们能行。现在去帮肖恩扣上裤子吧!”
维戈轻笑着,疲惫地站起身。“也祝你晚安。”
******
室内暗淡的灯光下,奥兰多温柔地微笑着,脚蜷在沙发上,双臂小心地搂着膝盖。他发出一声向往的叹息,电视里的音乐声变大了。
摸索到被半压在打盹的伊利亚身下的遥控器,他按下了倒回键。《蒂凡尼的早餐》在屏幕上快速倒回,他往后靠在垫子里,留意不要吵醒沙发另一头的伊利亚。
差不多九点了,他已十分疲惫。他猜想伊利亚要寄宿在他的公寓了,于是他任朋友蜷缩在沙发上,在睡梦中打着轻鼾。奥兰多坐在另一端,上床睡觉前他还有更多的事想做。
他蹑手蹑脚走进厨房,啪嗒打开灯,发现他的外套半搭在远处角落的一张椅子上。“好吧,”他咕哝着,把手伸进深深的口袋,掏出了那张折着的餐巾纸。
把它展开在桌上,他从墙上拿下电话,认真地盯着它。
“我不要多想,”奥兰多自言自语,按下了通话键,“我只要拨号……管它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是什么、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是什么。”
他的手有点抖,吞咽困难。未来的不确定让人大伤脑筋,而且也令他全身上下微微发抖。这是新鲜事,他人生中的大多数事情都是持续不变、可以预料的,这是件好事。
他的手指停留在键盘上,准备拨号,这时房间角落里一阵响动害他差点掉了电话。他畏缩了一下,双手握紧了滑落的电话,疼痛束缚着他的手指。
平稳下呼吸,他放下电话,看见猫咪穿过案台走来。
“噢,笨猫。”他低声说,抖开双手。猫咪正在翻看伊利亚留在案台上的打开的汤罐头。奥兰多叹口气,站起来。他训斥那大猫咪:“从那下来。你知道你不该在那上面。”
他皱着眉朝猫走过去,张开双臂想把它从案台上抓下来。那家伙另有打算,逃出奥兰多的掌握,跳到了冰箱上头。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奥兰多还在向前伸手,猫咪已经跳开,他裹着绷带的脚笨拙地踩到了洒出来的汤上。没等他能稳住自己,整个身体就猛地向前摔倒。
“该死。”他倒抽一口气,失去了平衡,盲目地伸手去够东西。他的手抓到了案台边,紧紧抓住,沿着光滑的木头猛然滑过。他忍不住喊起来,摩擦太剧烈了,以至于他的绷带散开,裸露的皮肤碰到了案台。
疼痛只能忍受几秒,而后他放开了手,带着一声空洞无声的哭喊跌倒在地板上。
他摊在那里,汤的汁水渗进了裤子,手撑在胸前。呼吸起伏不定,心口狂跳。他让自己平静下来,听见伊利亚柔和的鼾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
跌倒很疼,但是那疼痛没法和他手上的痛相比。眼泪止不住地滚落在他泛红的面颊上,木地板蒙住了少许的呜咽。
他曾经摔得比这次还惨,但是某种东西伤他更深。
“噢天啊,真惨。”他低语着,眼泪灼烧着皮肤。
他怎么还能想着会有不同的人生——一个可能与人分享的人生?他是多么的无用,多么的软弱,多么的需要完全依赖!
手上的疼痛会减轻,明早只会有背上、手上的少许水泡表明他曾摔倒。但是他不会忘记的。
他用衬衫袖子擦去眼泪,强迫自己坐起来。电话放在桌上,正好在他视线内。
他甚至想给维戈打电话,他简直蠢透了。现在他知道他必须打,但是是为不同的理由。
奥兰多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疼痛仍然很强烈。“记住这个,记住这疼痛。”他抓起电话想到。“永远都别忘记。你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你根本就不正常。”
甚至想都没想,他拨了那个号码,纹丝不动地站着,电话响了一声、两声、三声。
他甚至没有想他要说什么,之前他……不过现在他不会开心了。
然后电话应答机响了。
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我现在不在,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就在哔声后留言。”奥兰多吃惊地发现自己被那声音迷住了。
电话哔地响了,奥兰多尖叫了一小声,想让自己开口。“嗯,你好。”他咕哝着。好吧,一个良好有力的开端。现在让自己慢慢放松……“对,我是,嗯……总之,呃……再见。”
他尽可能快地挂上电话,呼吸急促。“我想还不错,”他说着把电话挂回去,“真是顺利啊,呸。”
一阵刺痛又在手上蔓延,他的眉头皱得更紧。厨房里的混乱可以等等再收拾,他筋疲力尽,只想着躲进自己房间里。
他走回客厅时伊利亚正坐起来,揉着眼睛。“你又在跟自己说话?”他睡意朦胧地问,咧嘴笑起来。
“事实上是的。”奥兰多有点酸涩地说,走向卧室。“你今晚在这过夜?”
伊利亚打着哈欠,他有点太疲倦了以至于没有察觉奥兰多低落的情绪。“如果没问题的话?”
“当然没问题,你知道毯子在哪。”奥兰多勉强露出笑容说。“咦,利加,你看起来很疲倦。”
“呆在你身边对我有不良影响,奥利。我发誓,我没准要变得作息正常了。”奥兰多叹口气,转过身,感觉眼泪再次涌上来。
他感觉自己太过情绪化了,犹如破碎了一般。伊利亚注意到了变化,现在更清醒些了,他心里责骂自己一贯公认的讥讽态度。看见奥兰多停在门口,他想到:“我从来都没有好好了解他。”
奥兰多打开了卧室门说:“晚安,利加,我会提早叫你,这样你就能在上班前蹦回你的地方去。”奥兰多只是微微笑笑,伊利亚回应他,希望奥兰多的情绪振奋起来。
“晚安,可爱的王子。”伊利亚逗他,换来奥兰多一个大大的微笑。
“你有神经病。”奥兰多从门后探出脑袋说。
“那作为精神病患者的最好朋友,该怎么说你们?”伊利亚猛捶了一下枕头问道。
“我同情那些不幸的人。”奥兰多揉揉鼻子答道。“晚安,你这疯子。”
伊利亚咕咕噜噜直叫唤,把枕头朝门丢过去。
“大事不好!”奥兰多尖叫着关上门,忍不住哈哈笑起来。不在伊利亚身边,他克制不住自己。“疯了。”他低声嘀咕。
“我听见了!”伊利亚喊起来。
“那就别站在那把耳朵贴在我门上,你五岁大啊。”奥兰多反击,笑得几乎喘不过气。伊利亚狠狠砸了一下门,然后一直打着哈欠,困乏地嘟囔了一句晚安。
奥兰多捡起伊利亚扔进他屋里的枕头,把它放在床脚。只是一个微小的动作就引发他手上微微的刺痛,笑容褪去了。
做了几个深呼吸,他准备面对一天中最艰难的部分——拆掉绷带。今年早些时候他甚至还不用在手脚上裹绷带。他十分注意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即使有小水泡也基本能正常生活。
但是随后他开始花了更多时间在图书馆,用手干更多的工作。手脚上的水泡恶化,但是他忽视了。医生曾告诉过他,等他年龄大了,水泡的严重程度很可能会减轻,于是他拒绝承认其实它们在不断恶化的事实。
只是最近,水泡发展成了感染,现在他尽可能多的包扎来帮助康复。这是一记无情的耳光,他只能怪自己。
每天晚上他都要解下绷带检查双手。他必须用消过毒的针扎破那些白天形成的水泡,然后在手指和脚趾上轻轻抹上药膏。拆绷带是一项极疼的任务,不管他事先在皮肤上涂了多少药膏,它们还是刺痛他的皮肤。
他尤其讨厌扎破水泡,那让皮肤痛得锥心刺骨,但这是他每晚例行公事的必经部分。如果他不刺破水泡,它们只会长得更大,变得危险又易感染。
他知道如果他想保持双手完好,就只能稍稍用手,他必须遵循时间表,每晚坚持,直到水泡减轻。
奥兰多坐在床上,小心地脱下短袜,挨着绷带微微弯起脚趾。这些日子他小心翼翼,但是脚通常还是受损严重,他无法足不沾地又保持独立。
他抬起一只脚放在床上,用左手抓住绷带末端。纱布好像永远也拆不完,今晚他没情绪去拖延疼痛。尽管纱布被润滑过,但经过一白天依然坚硬,变得有些难拆。他咬紧牙关,拉下一条长长的纱布。手疼脚痛,但至少这是短痛。
几滴眼泪滚落面颊,但是他不肯哭出来。他不想让伊利亚听到,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是多么脆弱。
他抬头看见镜中自己的双眼。“你不脆弱,你很坚强。”他说,但当他从另一只脚上拉下纱布,这些话成了空谈,汗水洇过了眉毛。唇间发出一小声啜泣,纱布脱落时双手抖个不停。
他的脚底和脚趾周围长了水泡。一些水泡破了,刺痛得厉害。他拿起针要挑破水泡,涂药膏时,他咬住舌头忍住可能要脱口而出的叫喊。
刺痛紧压着伤口,但是他必须做。
从手上拆纱布容易些,不过因为厨房里的小意外手伤得更重。腰也因为摔倒而疼痛,他预感过了今晚会形成一些小水泡。
手上的刺痛是如此剧烈,以至于右手失去了知觉,只是不停地颤动。他努力只用了二十分钟拆掉了手脚上的纱布,而后放松地蜷进床里,不受外来伤害,沐浴在幸福中。
这是艰难的一天,他要避开那些疼痛,那些失望。
他侧身蜷缩着,不理会手上一抽一抽的疼痛,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拉过一个枕头,紧紧搂在肚子上。
“晚安。”他低语着,眨眼间滑下一滴泪,他很快睡着了。
****
维戈拖着脚走进公寓,进门时踢掉了鞋,脱掉了外套。在如此漫长的一天后,回家的感觉真好,虽然他的家几乎并不能带来更多的舒适。
他没开灯,穿过房间溜到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一大瓶水。他深深地喝了几口,任思绪漫游。
公寓的设计布局在他记忆中根深蒂固,到今年秋天他已经住在这差不多五年了,他喜欢在黑暗中四处漫步。这令他感觉更加远离城市。
同样,他拥有的财富,漂亮的进口家具和设备,也让他有一点不自在。
维戈成长于一个迁徙家庭,他们从不会储存积蓄或是在乎他们所拥有。他们经常只在后备箱里放上衣服就去旅行,驻留或启程如同季节更替般稀松平常。
维戈在美国四处漂泊停留,还有欧洲的许多城市。奇怪的是,他最喜欢的地方是爱达荷:所有那些荒郊僻壤上的寂静黑夜让他真正的成长。
他哼了一声,斜靠着厨房的案台;从那之后他已走了多远!现在他拥有这世界的每一种奢华,还是孩子时他曾猜想它们能做什么,但是现在它们对他毫无意义。他仍然孤独,仍然空虚。工作已经变成他所一直担心的那样——只是一种达到结局的手段。
那结局正在一天天逼近。
于是,他不开灯,也许能忘记他的财富,忘记他的生活已然转变的模样。但是通常,黑暗只是隐没了墙壁,涂抹上未签名的画作。
走进客厅,渴望去阳台上抽根烟,电话应答机上闪烁的光亮吸引了他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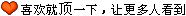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