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戈把他的大皮包放在塑料座椅下,用一根旧皮带把包系在脚踝上,他微微转身以便看见那个静静坐在身边的男人。年轻人没有注意他,注视着窗外,迷失在恍惚的思绪中。
虽然很无礼,维戈还是忍不住盯着年轻人微微弓起的身体。这可有点问题,有点不合时宜,有点变态下流。维戈随后转开脸,盯着同车的乏味男女。他们坐得笔管条直,目视前方,手插在口袋里或是拿着手机、报纸。
身边的陌生人动了一下,维戈的眼光又落回男人身上。偷瞥了一眼,就见男人的黑色外套下,脖根处围着一抹明亮的红色织物。维戈想起了秋日落叶和冷冽空气。这一次他没有移开目光。
年轻人双手抱胸,修长的双臂拢住纤细的身躯,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他的呼吸在窗上聚起了雾气。大体而言,他十分沉静,但是当维戈靠近端详时,他略显不安,眼光游走,贴着座椅摆腿。
在维戈右手的某处,拇指与食指之间,弯起的关节处,维戈有一种手握木质开裂的古旧画笔的感觉。维戈已经有几个月没画了,虽然早年间他酷爱绘画。他没有伤怀自己童年时代雄心壮志的消逝,只是任其慢慢淡出他的生活,循序渐进,以至不会留下怀旧之情。
很容易将年轻人视作一幅未完成的构图,首先聚焦区域,然后是细节。他经常以这种方式看人,以线条聚合他们,创造他们的动作与活力。
男人纤细的双臂是两条流动的线条,骄傲的下巴是一块黑色印迹。明亮的紫红色线条勾勒出他的形体,让他栩栩如生。他是模特,维戈注视着他,对他的线条构成着了迷。
奥兰多透过冰冷的厚玻璃注视着暗淡的城市,没注意维戈公然的打量,年长男人正在连接线条,建构美形。他正想着接下来的这一天:列车停站,步行到图书馆,在水泥台阶上跌倒。
这很容易变成打击,但是如果他预先筹划好一切,准确预见到之后会发生什么,他的不幸就会容易对付。
当然维戈对此一无所知,他是奥兰多路途中最未被计划在内的转变。
“有点颠簸,是吧?”
奥兰多猛地收回脑袋,立刻摆脱了幻想,一阵红晕蔓延上面颊。
“什么?”他轻声问,对上身边陌生人的温暖目光。维戈温和地笑笑,朝奥兰多探过脑袋。
“我说,这条线路有点颠簸,是不是?”
“噢,嗯……是的,”奥兰多乖乖作答,其实在嘈杂的车厢里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两人之间沉默了一会儿,奥兰多有种清晰的感觉,好奇的陌生人正等待他多一点的回答。“不过一直是这样,”奥兰多勉强开了口,看见维戈点了点头。“嗯,你很少乘吧?”
“为什么你会这么说?”维戈问,扬起一边眉毛,望着奥兰多慢慢放松自己,发觉他所采用的新姿势毫无不雅。奥兰多咬着嘴唇,微微困难地吞咽了一下,感觉自己贸然开口真是愚蠢。
“哦,只是,多数人,嗯,我想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在地铁上和陌生人攀谈,”奥兰多笨拙地说,他抬起头,发觉年长男人直盯着他,他再次垂下眼。“那样很生硬……”
“啊,我明白了。”维戈微微笑了笑答道。他看得出奥兰多下巴绷紧,肌肉抽搐,牙关紧咬。年轻人显然很不安,维戈觉得自己对他的不安负有一些责任,着手消除。他非常善于掌控人,能巧妙地让人得其所哉。
奥兰多在座位上不安地动来动去,忍不住抬头看,发现维戈眼中闪烁着欢乐的光芒。那目光霎时间温暖了奥兰多的肺腑,抑制了他胸中的不安。
维戈能感觉到奥兰多的举动缓和下来,年轻人放松地靠在座位上。
“这是不是地铁礼仪?”维戈像是深思熟虑般地问道,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奥兰多。“如果我们都假装盯着地板,闭上嘴,那么人们怎么相遇?我问你,当我谈论这个话题时,我无法相信像你这样的人每天不会碰上数不胜数的有失礼貌的攀谈。这太愚蠢了。”他浅吸了口气,笑嘻嘻地说,“这话可真啰嗦。”
奥兰多的脸更红了,目光瞟向脚面,而后又抬眼接近陌生人微笑的目光。
“是的。”奥兰多终于回应,几近耳语。
“你是指有陌生人在地铁上搭讪你,还是指这话啰嗦?我觉得我自己是有点啰嗦。”维戈承认,眉毛询问似地挑了挑。他的一只胳膊肘往后搭在椅背上,无意识地侵入了奥兰多的私人空间。
“这要看别人寻求的是什么,”奥兰多脱口而出,在座位里稍稍后移,留心看着维戈的前臂。“我是说……我拿不准你的意思……不过我每天早晨会给车站外蹲着的人一些硬币。我想那也许有帮助。不过说到底他们也许没把钱花在有益健康的事上,这似乎有点想当然,首先是什么让他们流落街头?哦胡扯,我在说什么呢?我……”他张口结舌,再次徒劳地想表白自己。
“那么你应该更常被搭讪,”维戈歪着脑袋随意说道。奥兰多皱起眉头,维戈咧嘴一笑,靠得更近些,想要看看奥兰多脸颊上升腾起的红晕。这个距离对奥兰多而言有点可怕,不过他们之间仍有一段相当的距离。“也许你的硬币会终结纽约城的饥饿,或者至少是对精神的渴求。”他继续说,脱下了自己的手套,把手插进了外套口袋。“那么我对你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是’。因为今早的疯狂交通,我是第一次乘这条线,我通常开车进城。我叫维戈·莫滕森。”维戈伸出了手,虽然奥兰多像了解地铁变化一样了解社交礼仪,但他的手还是坚决地放在腿上。
“我叫奥兰多·布鲁姆。”他礼貌地说,维戈垂下手,意识到奥兰多没打算回应他的握手。令人惊讶的是,奥兰多发现维戈不仅真的很有意思,而且难以预料——不过,如果他对自己够坦诚,其实那也是有意思的部分。只是这个认知让他失去了勇气。
无论如何,察觉这个男人富于魅力并不让奥兰多惊讶。他一直知道自己的偏好,也从未担心因为自己的性向可能招致的污名。他成长在自由开明的伦敦,懂得对每日每刻心怀感激。
这就是他。
他曾对自己发誓,不会让心动折磨他,迄今为止,这是一个易于保守的誓言。亲密关系从来都不是他生活中的现实要素:人们避开这位黑眼美人,害怕碰碎这个“玻璃人”。至少这些是他喜欢对自己说的。他不想对自己承认,也许是他避开了其他人。
当他意图躲开旁人,害怕被拒绝被伤害时,奥兰多甚至很难维持友谊。遇见伊利亚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例外,奥兰多被图书馆雇佣后,他们立即就粘在了一起。
奥兰多不易察觉地离维戈远些,望着建筑楼顶在远景中倒退,目光慢慢放松又回到那迷人的男人身上。
只这一眼,他就知道坐在身边的男人相当大了:微笑的淡蓝色眼睛和温柔的嘴边都有细细的纹路透露了年龄。沿着男人的鬓角能看见一点灰白散布在深蜜色的头发中。奥兰多猜维戈大概四十出头,年龄差有点惊人时,也意味着双倍的吸引力。
毫无疑问,他很精神。英俊醒目的面庞,厚重衣服下依然轮廓分明的体型,奥兰多暗自评估这个男人,不禁脸红起来。
而后抬起眼,再次遇上维戈的目光,奥兰多发觉自己不知说什么好。“哦,嗯……你开车进城?那你到底怎么在城里找到停车位?”他有点结巴地问道。
奥兰多不太擅长未准备的交谈,他最多的社交往来是和伊利亚还有图书馆的孩子们,但是他也并非一直不知所措。他只不过是发现和孩子们交谈最容易,那是他的工作,也更加充实了他的生活。在奥兰多看来,孩子们不是审判者,他们只是……充满了无尽的好奇。
如果他们问起奥兰多的绷带或是擦伤,他们就开门见山,而他总是很乐于回答。
一旦好奇心得到满足,他们对差别也就熟视无睹。相反,当绷带很显眼时,多数人通常不会接近奥兰多——他们只不过是疑问地偷偷瞟上几眼,一群人自己在那窃窃私语,好像他不会注意到似的。现在无论他是包扎着还是有明显的擦伤,戴手套已是一种习惯,即使天气很热。
“我的楼外有一块备用场地。”维戈解释道,令奥兰多摆脱了沉思。维戈稍作停顿,期待地望着奥兰多,不过他并未真打算要深入这个话题。奥兰多猛一抬头,眼中流露出一丝惊慌。
“哦?”奥兰多说不出别的。
“好,你不想多谈,是吧?”维戈咧嘴一笑,奥兰多面红耳赤。奥兰多感觉得出,这男人有把坏事说好的诀窍。
“嗯……”
“对不起,”维戈说,“我老是自动假设人人都想和我交谈。我有点自我中心,老管不住烦人的舌头,不时会发作一下。请你随意,完全不用理我。”他仍就笑着,奥兰多发现那笑容有种奇特的感染力。“不是这样?你还在微笑?好吧,我没事了。”
“我想你会没事的。”奥兰多非常轻声地回答,维戈不得不靠近过来捕捉那柔软甜美的声音。维戈发觉自己奇怪地被年轻人所吸引,虽然他们几乎没有深谈。也许是因为男人有某种持久而安静的东西。
‘但是安静真的不是形容某人的方式,’维戈仍旧笑着思索。这是上午9点前的第一个露齿笑容。“谢谢你,这绝对是……一次受伤的体验,”维戈佯装严肃地说,“我欠了你……奥兰多。”沉默之人的名字在维戈口中如此完美的契合,如同熟读的诗句一般脱口而出。
“没有,”奥兰多笑起来,对自己发出连串的笑声也有点惊讶。“显然你是孤军作战。我只是坐在这,差点打了个盹,真的。”
维戈佯装愤慨,奥兰多不禁惊奇于自己与微笑的陌生人交谈时的放松。奥兰多微微探过身,放松绷紧的双手。也许维戈的超凡自信有感染力。
“那你‘打了个盹’?”维戈动了动问道。“我想你是英国人,不过我很难发好你的重音。我们切尔西区的好多人鼻子扬得太高,你准会说那对声带有影响。这样就好像我们都是古板世故的来自大洋彼岸的贵族。噢,我收回这话,我们太轻浮成不了贵族。也许绅士还差不多。是吧,英国人?”
“是的。”奥兰多微微低下头,希望能避开关于此话题的更多问题,这时列车晃动着刹了车。一些乘客下了车,奥兰多重又抬头看维戈,维戈仍就一直看着他。
“我可以问问你在纽约做什么吗?度假?”列车再次启动,奥兰多在座位里用右手轻轻撑住自己,忽略了蔓延在手掌上的刺痛。他通常不用这么小心自己双手的活动,他发现自己正学会小心应对艰难的情况。
“不,我住在这,当然不是你看见的这里。我是说,这里是车厢。嗯,我不想多谈这个。”奥兰多猛然闭上嘴,转开脸。
“我相信你通常很健谈。”维戈说,他的语调温暖而确信。“我就是那种阴郁悲观、沉思默想、让人不知所措的类型,你知道的。太让人心烦。啊,我想我是没治了。”
“那可悲剧了,”奥兰多发觉自己说道,“阴郁悲观、沉思默想,一个自大狂。我完全怀疑我会和你交谈。”他微微一笑,斜靠近维戈肩膀的举动背叛了他声音里的冷淡。
“哦,你不喜欢沉思默想?我发誓,那是第一位的。阴郁悲观、有点高深莫测怎么样?我想我就这样。这是你喜欢的类型吗?”维戈的声音略略放低,更加亲密。
“我没有喜欢的类型。”奥兰多诚实作答。
“说吧。她该什么样?”
“我……该死!”奥兰多叫起来,在座位上转来转去,沉重叹息。
“噢?”
“不,我坐过了站。该死……对不起,我是说……嗯。”奥兰多在位子上扭动得更厉害了,留意着他受伤的手,看着列车驶进了亚斯特坊广场站。“噢,不……”
“你本打算在哪下车?”维戈问,从他的胸前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地铁线路图,轻轻敲敲奥兰多的肩膀。奥兰多抓住车窗框的手滑了一下,他稳住自己,手因为摩擦灼痛起来。他吸了口气,抬起手,忍住了想脱口而出的轻声喊叫。仅仅是一个撞击,但疼痛剧烈。奥兰多能感觉到眼泪涌了上来。
“索……索霍站,”他勉强说道,松了口气——维戈正在研究那大地图而没注意到他的小小意外。‘呼吸’,他对自己说,‘现在不能失去呼吸。’
“这地图……不可能啊,我不明白……”维戈痛苦地喃喃自语。
“别担心。”奥兰多咬着牙说,抬起左臂小心地擦了擦他的眼睛。大滴的眼泪弄脏了他的面颊,已然玫瑰色的皮肤变得更红。“只是我现在必须下车,上二十分钟内反方向的列车。”他平静地说,稳住手,腿因为忍痛而有些颤抖。“所以,我到站了……”他虚弱地站起身,朝维戈微微点点头。他现在只想要下车,找一个卫生间,好好大哭一场,然后给伊利亚打电话。维戈抬头看着他微笑起来,完全没有觉察。
“好吧,”维戈答道,明显对地图没辙了,他带着一副好笑的挫败愁容,将地图塞进了外套口袋,“想不想在等车的时候来杯咖啡?”
“可是……”奥兰多结结巴巴地说,等着排队的乘客下车,而后走向车门。他拼命想离开维戈的视线,他需要镇定自己,驱走胸中难以抑制的焦虑不安。“你到站了?”
“当然,”维戈说着将一只手轻轻按在奥兰多的背上,就在肩胛骨中间。奥兰多没有计较这前推的动作和柔和的压力,让维戈领他下了车,站到了忙碌的站台上。
“我……需要去趟洗手间。”奥兰多说,稍稍远离开移动的人群。“对不起。”维戈放下手,奥兰多立刻溜出了视线。
“等等,”维戈搜寻的声音传来,奥兰多转回身,逆着移动的人流。“你掉了东西!”奥兰多吞咽了一下,挣扎着向前靠近维戈。一个大个子男人抓着笨重的黑公文包,猛地撞在奥兰多肩膀上,年轻人摇摇晃晃地往左闪。
“嘿,当心。”维戈对那一脸愁容的男人皱了皱眉,很快地将奥兰多拉出了拥挤人群的中心。他拉着年轻人到站台一边,站在破旧的铁制长椅后。
“我……掉了什么?”奥兰多畏缩地问。
“这儿呢,”维戈咕哝着,像是避免惊吓似的缓慢小心地抬起他的手,两根手指间捏起的是薄薄的纸片。奥兰多只能点点头,出乎自己意料地伸出了隐藏的手,维戈翻开手掌,结茧的拇指抚过年轻人的面颊。“等一下……”他喃喃说着,奥兰多继续目视下方,无法看着维戈的眼睛。奥兰多感觉维戈温暖的肌肤拭去了他脸颊上冰凉潮湿的痕迹。“今天早上的风真糟糕,”维戈说,奥兰多又点点头。片刻间奥兰多忘记了手上的刺痛,新的眼泪滚下面颊——只能全神贯注于维戈拇指如此轻柔的抚摸。
相比于在列车上,如此接近的距离里奥兰多更能闻到维戈的气息,他散发着浓烈的麝香味道。奥兰多嫉妒地意识到,年长男人非常的吸引人。他身上有某种强烈的东西,坦率而强势——虽然那大多隐藏在优美的外表下。奥兰多几乎不了解这个男人,但是他看得出。他想倾身接近,靠在维戈温暖的脖颈上深呼吸。
这个念头惊到了奥兰多,回归现实,他的手在颤动,他几乎是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哭泣。
“对不起,”奥兰多退开来,嘶哑地说。维戈的手落到身旁,奥兰多立刻心怀歉意。“洗手间。我……我就一会儿,我要……”
“拿着这个,”维戈温柔地说,没在意奥兰多疲惫的举动,他再次张开手露出了一张微皱的书签。奥兰多立刻认了出来,那是图书馆阅读小组里一个小孩子送他的礼物。书签是亮桔色的,顶端带着一条小蓝穗,上面画着“小熊维尼”中的几个人物。“你把这个掉在站台上了,恐怕有点折了。”
“谢谢。”奥兰多含糊地说,笨拙地拿起了书签。他差点又把书签弄掉了,而后他把书签深深插进外套口袋中。“我要……
“在对面天井的时钟旁见我怎么样?”维戈提议,朝那个大黄铜钟歪歪脑袋。奥兰多肯定地点点头,尽可能快地挤过人群,他需要距离,需要一个人呆着。
他释放地长叹一声溜进卫生间,发现里面没人。斜靠着水池,手肘抵着瓷盆,他任眼泪释放而出。他的手几乎不抖了,但是这局面让他心绪难平。
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在公众场合情绪崩溃了,其实主要是由于他几乎不再出家门——除了每周购物,那还是有伊利亚的陪伴。
“噢天啊,太惨了。”他抱怨着,做了几个深呼吸,抖开了手。他脱下右手的手套,检查纱布,发现那些破口水泡的湿气所造成的灰白色没有加深。他的手刺痛多是在水泡破了以后。他大大松了口气,套回手套,呼吸更加平稳。
他抬头看镜子,轻轻抹去干涸的泪痕,虚弱地笑笑,他想起维戈就在几分钟前所做的同样举动。“噢,你这个笨蛋。”他对着自己的投影说,不过笑容却更加灿烂。
就在这时,门啪的一声打开,清洁工带着拖把、推车走进来。奥兰多最后看了眼镜子,擦去前额上亮闪闪的湿气,从清洁工身边挤了出去。
他闪进卫生间外的一小排电话亭,从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他拨了伊利亚的号码,靠在墙上等待。
“纽约公共图书馆分部索霍区公共图书馆,我是伊利亚·伍德,”伊利亚老练的应答传来,“我能为您效劳吗?”
“是我,你可以放松了。”奥兰多轻轻笑着说。
“噢,是你啊,”伊利亚哼了一声,奥兰多完全可以描绘出他朋友的样子:脚搭在桌上,胸口上放着吃了一半的油炸圈,明亮的蓝眼睛叽里咕噜乱转。“既然这样,你到底想干嘛?”伊利亚问道,刺耳的腔调下潜伏着欢喜。奥兰多忍不住又笑起来,伊利亚愤愤地说:“严肃点,怎么了?”
“我要稍微迟到会儿,我坐过站了。我现在在亚斯特坊广场站。”奥兰多解释说,因为电话和弦音而心烦。
“你怎么搞的?”伊利亚问,啧啧有声,他无疑是在享用今早的第三杯咖啡。
“我心不在焉了。”奥兰多答道,说这话时他感觉自己脸红了。
“你每天早上都走这条线,奥利。”
“可从没在星期三乘过。”奥兰多点明。
“少来,那有什么关系。你还好吗?”听起来伊利亚开始担心了,奥兰多叹息着,决定让他知道一点今早的事。
“你担心太多了,我很好。我只是……和别人说话……错过了到站时间。”他尽量平淡,但伊利亚低低吹了声口哨,奥兰多叹了口气。
“冷静的奥兰多心烦意乱了?准是个女孩。”
“不是的,利加,”奥兰多叹口气,“只是一些……一些有趣的交谈。”
“等你到的时候你要原原本本告诉我。”伊利亚强调说,又动静很大地喝了一大口咖啡。
“不行,绝对不行。就是说说话。人人都会这么做,天啊,我们别太夸张了。”
“奥兰多,你现在应该知道,我凡事都夸张。我讨厌提醒你,但是你很不正常。我回马萨诸塞州见你时你还害羞得要死。这事值得庆贺。也许她会拉着你到处转,带你去杂货店购物,嗯,我可以歇一周啦?”伊利亚逗他,奥兰多高声哀鸣。
“我必须得走了,利加,我要确定别错过下一趟车。”奥兰多长叹一声说。
“好吧。但是等会儿你得告诉我。”
“好,好!现在去干点正事,你这个傻瓜。”奥兰多微微笑着训他。
“好吧,好吧。等会儿见。”伊利亚满口塞着东西说,奥兰多知道那是草莓果酱油炸圈——伊利亚的标志性早餐。
“好的,”奥兰多嘟囔着,举起电话夹在肩膀和耳朵间,“噢,利加?”
“呣?”
奥兰多露齿一笑:“不是什么女孩。”
“等等……什么?”
“回见。”
“奥兰——”
奥兰多心满意足地一弹舌尖,挂上了电话,他几乎忍不住要哈哈笑出来。他纵容自己大笑,因为今天真的进展不错。
他把双手插进口袋,再次走入人群,他有某种奇特又挺不错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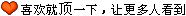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