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題作文 《彼岸花》
在離開木葉之後鼬偶爾會有這樣的念頭。
要是能晚點兒離開就好了。
比起他年幼時所渴望的那些事情,這幾個簡單的字眼聽起來似乎更加的諷刺。
所以那小小的聲音只是偶爾的從那些重重疊疊的暗淡過往中稍微的冒出些頭來,微弱的喧鬧著,然后便被迅速而無情的扑滅了。
離開畢竟是離開了。事到如今,在他心裡面,沒甚麼是可以輓回的。
就算是在月讀的世界裡也是如此。
只是隨著歲月的流逝,與世隔離的曉,和木葉那個讓人無法喘息的世界,正在漸漸的重疊起來。
變得同樣讓他不能忍受起來。
這些事情,緩慢的發生著,好像那些不知不覺便失去的過往,好像他回憶裡那些漸漸暗淡的顏色。
晓有着迷宫一般的走廊。那些木地板在空气中散發著沉默的味道,在有人經過的時候,輕微的呻吟著,那細弱的咯吱聲好像是怕惊動了什么似的匍匐在塵土之中。
走廊上没有照明的烛或者松節,因为以前曾经失过火,一切能夠引起火災的小小因子都被排除地一干二凈了。
要是正午或者夕陽還未下山時回來,那走廊上淡白地松木紋理仍舊映著橘紅色地柔光,緩慢地推移著,慢慢的落在那不見光地角落里,然后掉了下去。
這個小小的世界同外面的那個沒什么不同。
也會黑天,也會入夜,入夜的話,也會有月光。
那疏离的白色月光雖然可以照亮那迷宮般的走廊,卻一同照亮了夜晚應當休憩的地方。
每次执行完任务後,都要經過那迷宫一样的回廊,有時候他甚至會有奇怪的錯覺,似乎那散發著陳腐味道的木牆會如同碎沙一樣瞬時間的倒塌下來,那走廊不知哪里會腐爛而經不起踐踏,只是晓的人似乎从来不会迷路,顺便也遗忘了这走廊的幽暗吧。 他從未听到其他的人對這居所有所抱怨,于是他也沉默不語。
收容了那些S級逃忍的曉,總是從各國的大名那里接一些稀奇古怪講不出口的任務,木然的按照指示去完成那些任務的鼬,回來之后第一件事同別人一樣,是向首領報告任務的完成情況。
報告完畢,才能回到那一方小小的和室。
只不过六席宽的房间里其實什么也没有,就算閉著雙眼他也能完整的走回去,寫輪眼在這种時候用起來似乎就象玩具。
他在那沉重的黑暗中径直的走过去,停在自己的那一間,然后胡亂的拉开纸门走進去。
他只是這樣盘著腿坐在房间的正中,安静的看着紙門外。
每次出任務回來後,衣服上總是帶著奇怪的味道。
潮濕水气的味道,被苦無割斷的青草味道,淡淡金屬生鏽的味道,偶爾會有新鮮血液的味道,他難免會有不小心的時候。
看得到月光的時候,房間里那通澈的明亮,簡直陌生的讓人惶恐。
初秋的時候,山谷里夜露深重,紙門大大拉開的時候,夜風夾攜著愁苦的寒意涌入那小小的和室,他靜靜的坐在那里,直到身上的味道同夜晚一樣冰涼。
在曉呆了不到一年,冬天的時候,他開始覺得疲憊,但是仔細想想他的年紀,似乎還沒有大到可以稱做老的地步。
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首領要他同鬼鲛搭檔。
鬼鲛這個人似乎有使不盡的力气,無論什么任務都躍躍欲試,鼬雖然不太喜歡他殺人的熱情,但是權衡了一下利弊,還是選擇了在鬼鲛動手時站在一旁觀望的協作方式,同時安靜的閉嘴。
他總覺得自己身体有什么在慢慢的老去,安靜的連喘息聲都听不到。
每當他回到那小小的和室里時,閉上雙眼,就會覺得掉落在了不知道是誰的幻境里。
那些猶如野草一樣干枯而荒茫的力量,從那個暗紅色的世界里一層層的蔓延著,瘋狂又迷惑的隨風搖擺,那是陌生而強悍的力量,那是荒蕪又饑渴的力量。
他所要等待的那一天看起來是那么的遙遠,只是有時擔心,恐怕等不到那一刻他就已經僵老而死。
被那片暗紅色荒原上紅花的尸体所覆蓋,干涸而迷茫的死去。
記得有一次他這樣問鬼鲛,“如果不介意的話,我想問你為什么會來曉。”
宇智波家族良好而嚴格的教育至今還在他的身上留有烙印,鬼鲛擺擺手隨便的說不要這么客气。
他眉毛一動不動,等著听男人的回答。
“……也許是 ……想看看自己究竟能有多厲害吧。”抱著臂站在他身前的男人,側影看起來熟悉的讓人迷惑。
那是似曾相識的回答,至于那答案到底有多少發自內心,那便是不得而知的隱秘了。
但是他卻沒有想到,這番對話卻引起了那男人之前未曾表露分毫的好奇心,鬼鲛似乎是毫不在意的問他:“听說你殺了什么人才拿到這雙眼睛的?”
霧隱的男人,問出這話來的時候,沒有絲毫的遲疑,他后來努力的回想了一下當時的場景,鬼鲛那雙青色的眼睛里涌動的似乎不只是好奇,那种太過明顯的自以為是強烈得几乎令他覺得不快。
他的确是這么對佐助說的。
是他殺掉了止水。
在宇智波滅族的那個夜晚,在他親手做出的幻境里,在那片血紅色的月讀空間里。
他似乎只對佐助這么說過吧?他不記得他還對別的什么人說過相同的話,記憶在他的大腦里与他親手做出來的月讀空間混淆成了一片。
那雙青色的眼睛漸漸的靠近了他,如同饑餓的狼步步逼近著自己的獵物,那种凶殘而天真的笑容在那張猙獰的面目上越發的清晰了起來。
“你听誰說的?”他一動不動的站在那里,絲毫也不層后退。
“唉呀,你們村子里傳出來的啊。”鬼鲛一臉的理所當然。
腦海里那渾濁一片的回憶突然的清晰了起來。那些前來質問止水死因的長輩,還有父親自以為是的賭咒發誓。
還有佐助那落在紙牆陰影里惶恐的臉。
“哦。”他冷漠的回答道。
“是你殺的嗎?那個……叫什么的?”鬼鲛撓了撓臉。
“止水,宇智波止水。”他看了一眼鬼鲛的手,不動聲色的回答說。“他是掉在河里淹死的。”
鬼鲛呵呵的笑了起來,大概以為自己在騙他吧。
“那你怎么得到這雙眼睛的?”
他抬起頭來,一個字一個字認真的對著那男人說:“我對他用了寫輪眼。”
這對話便如他所想的到此結束了。只是鬼鲛臉上那副果然不出我所料的表情讓他稍微的想了想,但畢竟還是安靜的結束了。
他從以前,就習慣与人遠遠的隔開。
就算是快要死了,也不肯拉住別人伸過來的手。
這是個頑固的坏毛病,可惜在族規森嚴的木葉都未能糾正,于是這偏斜的枝干在曉便更加愉快而肆無忌憚的伸展開來了。
他從小就不太受族人的喜歡,雖然最初并未察覺但是漸漸的便會發現,和顏悅色与敬而遠之的區別,大笑著揉亂孩子頭發同嚴肅面對的不同。
畢竟這些算不上細微的詫异。
但不幸的是,除卻了忍術上的天才,他只是一個遲鈍的孩子。
他安靜的行走在眾人之間,毫不在意的給家族帶來榮耀和驕傲,參与那些与他年齡不符的任務和行動,沉默的几乎讓人忘記了他真實的年齡。
那時他是父母唯一的孩子,那些完全不屬于五歲孩子的沉默与安靜令雙親對他望而卻步,同齡人中他看不到值得交往的朋友,前輩与長輩都只會說一些冠冕堂皇死气沉沉的話,每次經過那些人的身邊都會聞到腐朽的气息,令他只想快步繞過。
但也總有繞不過去的時候,于是就有那么一次,恭敬的站在一旁不知道听那些老人在講什么的短發男人,用力的抓住了他的手臂,微笑著對他說道:見到長輩要問好。
同樣的團扇標志,丑陋而僵硬的印在那男人后心的位置,如果瞄准那個位置刺穿的話,就會立刻斃命吧。
他想了想,松開了已經握緊的拳頭,淡淡的道著歉,問好,然后离開了。
那是他還不知道,那男人是一個遠比他強大的宇智波。
后來仍舊會裝作沒看到的走過去,再次被那男人捉住後,他頗覺有趣的看了那人一眼。
“小孩子要懂禮貌啊。”那男人只是點點頭這么對他說道。
年輕男人的名字叫做宇智波止水,對于一聲不響跟在自己身后走進森林的鼬,也只是在站定了之后頭也不回的問道:
“你想報复嗎?”
他站在高高的樹上,有些吃惊。
男人轉過身來,朝他所隱藏的地方愉快的笑了起來。
“我叫宇智波止水,你可要記清楚啊!”
那時候,他只不過五歲。
記憶里那時的男人有著高大的背影,其實推算起來那時也只不過是個剛成年不久的孩子而已。
但是走到那男人身邊的時候,重重疊疊的樹影從天空中落下來,猶如潮濕的蛛网,夢一樣的跌落在他的額頭上,他要仰著頭,才能夠看到那男人輪廓分明的臉。
揉亂了他的頭發之后這才好像想起來什么似的問他“你叫什么?”
他愣了一下。
從未有人問過他這樣的問題。
他是鼬,宇智波鼬,木葉村里有誰不知道?
就算他每天都只是低著頭走過木葉的街道,就算他根本不知道這村子里都有誰和誰。
男人微微的皺起了眉頭,自言自語般的低聲說道:“唉呀,不會是笨蛋吧。”
“鼬,宇智波鼬,”他有些急促的脫口而出,卻不知道為了什么。
“噯……”男人怔了一下,想了想,然后馬馬虎虎的說道:“哦 ,知道了。”
他別扭的站在那里,看著男人略顯疲憊的側臉。
大概人類就是這樣的渺小和淺薄吧。
后來的他慢慢的回想著,如果那男人的身上沒有那种掩蓋在漫不經心下的傲慢,如果那男人不是宇智波家族里最強的男人,如果那男人不是那樣強勁的捉住了他的手腕……
他還會不會緊跟著對方不放。
只可惜……
那些早已消逝的過去沒有如果。
那時仍舊沒有离開學校的鼬,每天跟隨著學校里的中忍老師在村子里拔草,巡邏,尋找走失的羊,修補漏雨的屋頂,為了那些瑣碎的事情灰頭土臉。
那些明明是下忍所作的事情,卻因為戰爭的逼迫,全部都移交到了他們這些連下忍都算不上的孩子頭上。
他用湖水清洗著臉上的污臟,安靜的看著湖面上一波波細小的水紋里滴落著水珠的面孔,還有那雙血紅色的眼睛。
會霉爛掉的。他自言自語般的說道。
那就晒晒太陽好了。男人興味索然的聲音從高處落了下來。
他猛然的轉身。
男人跳了下來,“從今天起我要看著你哪,你可給我老實點。”
他只是微微的眯起了眼。
“真是……”男人撓了撓脖子苦悶的抱怨了起來,“讓我來看孩子。”
他安靜的看著男人朝他走來。那是所有的宇智波都有的眼眸,漆黑烏亮,猶如烏鴉的翅膀。
那么直白的告訴了鼬,我是來監視你的。
戰斗時應該會張開那雙血紅色的眼瞳吧。
“你老實一點,我也輕松一點,”男人揉了揉他的頭發,走過他身旁的時候,把一把苦無扔在了他的手里。
他沉默不語的把那苦無收回在原本的位置。
“明白了?”
他看到那男人回過了頭,對他露出那与長輩面前截然不同的表情來,那是冷淡的面容。
五歲的鼬,還未學會拒絕。
比如說。
他本來早就應該离開忍者學校的,有趣的是,族里的長老卻通過父親向他傳話說:再呆兩年吧。
還不懂得要如何面對父親命令的鼬,就那樣留在了學校里,直到兩年後才終于迎來畢業的那一刻。
雖然如此,那男人也只不過是偶爾的出現在他的身旁,用毫無威脅的聲音扑滅他腦袋里某些蠢蠢欲動的念頭,然后揉著他的腦袋。
那時他還不知道,族里的長老和前輩們,放了怎樣的一個人來看守他。
身在暗部的止水,年幼時曾經算是個性格乖僻的人,升中忍之前一直与后來成為四代目的男人分在同組,也許是因為那樣,所以比起其他的宇智波,在村子里反而不太出名。
但是他曾經听到父親親口讚揚那個叫做止水的宇智波。
同時暗暗的抱怨說:“讓自來也帶那孩子,實在是太可惜了。 ”
那种長輩之間私下里的牢騷,雖然只是偶爾說說,卻清晰的落在了鼬的心里。
能讓一向謹言慎行的父親說出這樣的話來,他對那名字的主人生出了微小的好奇。
在暗部任分隊長的止水,看起來似乎是個安靜而不喜張揚的人,總是帶著白色的狐狸面具,那張猶如笑臉一般的面具摘下來的時候,鼬覺得自己似乎看到了湖水中自己的倒影。
血紅色的雙眸漸漸的轉黑,好像咆哮著的野獸突然間困倦的收回了利爪,整個戰場安宁平和的好像清晨的湖面。
他控制著自己的呼吸,看著那男人毫不眷戀的离去。
尾隨止水執行暗部任務的事情他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過,雖然被那男人寫輪眼的威力所震懾,但想到一路跟蹤的自己居然未被發現便覺得不快。
原來父親所看到的人,也不過如此。
那時候因為學校的無趣所以經常自己帶著苦無和手里劍去森林練習,臨走前母親突然站在玄關前有些忐忑的問他道:鼬想不想要個弟弟呢?
他站住了,看著母親有些緊張的笑臉,想了一下。
母親走上前來,黑色的頭發垂了下來遮住了額角,溫柔的聲音里有微小的恐懼。
鼬,媽媽替你生個弟弟好嗎?
那是難以察覺的顫抖,鼬不禁覺得奇怪,究竟是哪里,自己究竟是哪里做的不好呢?
五歲的鼬,雖然迷惑,卻還是用宛如平常的口吻回答說好。
母親暗暗的松了一口气,在他的身后露出了哀傷的笑臉。
站在他的身后,一直注視著他离去的母親,直到他走出了很遠這才回到屋內,他抬起了頭,緋紅色的寫輪眼漸漸的沉淀為黑色。
弟弟嗎?
他想。
父親和母親并不常提起這件事情,但是的确曾經明白的告訴過他,弟弟的名字已經取好。
父親給那孩子取名叫做佐助。
那名字,讓人想起猿飛佐助,那個傳奇般的男人。
SUKE。
佐也好,助也好,都念做SUKE啊…… 到底父親想要從那么渺小的希望里得到什么樣的佐助呢?
為尚未出生的孩子取了這樣名字的父親,心底究竟有些什么樣的期許,那是五歲的鼬不得而知的。
但是發覺這一切,卻是在佐助出生後。
母親的任務量漸漸的少得令人怀疑起來,到了七月那潮濕的季節,他終于迎來了血緣相系的弟弟。
那時的他尚不明了那孩子出生的意義。
一直以來,似乎只有很少的宇智波才擁有血脈相連的兄弟姐妹,五歲的他,并不知道母親忍受著妊娠和分娩的痛苦所帶來的那個孩子,究竟對他意味著什么。
剛剛出生的孩子,肮臟而丑陋,皺皺的粉紅色看起來就讓人厭惡,母親卻把那小小的東西小心的摟在胸前,疼惜的注視著。
站在母親的身邊,難以言說的心情無法表達,所以和平常一樣的沉默著,母親微笑著把那個小東西遞到他的面前,用溫柔而親熱的口吻問他要不要看一眼弟弟。
雖然并沒有想要伸手抱抱那孩子的念頭,但是母親眼底的歡喜,只會令他覺得莫名煩躁而已。
家里的人都忙于應付那個幼小的生命,無所事事的他一個人安靜的坐在走廊上,听著那人群快活而忙碌的喧鬧聲。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夜晚變的悶熱,走廊上的晴天娃娃一動不動的歪著頭看他,他閉上了眼睛。
他离開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注意到。
他沒有出聲就拉開了那扇單薄的紙門,站在止水面前後,看到那男人正在沉默的擦拭著一柄短小的苦無,簡陋的木几上整齊的一字排著几十把相同式樣的鐵器。
“你弟弟今天出生了吧?”止水抬起頭來掃了他一眼,一本正經的對他說道:“真羡慕你啊。”
他有些困惑,不明白那突然嚴肅起來的男人在說什么奇怪的話。
“你走過的彎路,要讓他好好避開。”
他的胸口被什么東西猛烈的敲痛了,他警惕又期待的看著那男人的側臉。
“人要蠢一點才行。”男人把苦無舉了起來,那薄薄的光從鐵刃上滑落下來,有轉瞬既逝的笑容印在鼬的眼底。“好好的照顧他吧。”
那并不是嘲諷般的嗤笑。
“要是我也有一個弟弟,或者妹妹的話,”男人手里的苦無隨意的拋了出去,擦過他的耳廓,扎在紙門上。
他听到紙門吱呀的猶豫了一下,然后柔軟的倒落了下去。
“也許我會更拼命點……保護木葉吧。”男人的表情,難以形容。
他只記得,那紙門倒地后,如同激流一樣洶涌淹沒他們的月光,明亮的讓人惶恐。
“教我吧。”他突然開口道。“教我你的手里劍和苦無。”
“你不是……挺好嗎?”男人端正的坐在他的面前,端詳著他的臉。
“教我吧。”他頑固的堅持道。
月光里男人那張輪廓柔和的臉變得堅硬了起來,他覺得自己的身体在隨著胸口的震動而劇烈的顫抖著,那么的明顯。
就算到了最后,他也沒有听到肯定的答复。
但是那天之后,他開始固執而沉默的跟著那男人了。
那時接連不斷的戰爭并沒有給木葉帶來什么,死去的人一個接著一個,有很多的忍者就那樣埋葬在了荒蕪的戰場上,還有更多的人連尸体都未找到。
一直呆在那种保育院一樣的忍者學校里,戰爭中所發生的一切也不時的傳到他們的耳中。
回憶中仍舊留有印象的,是木葉的天才忍者得到了寫輪眼的消息,与之一同回到村子里的,還有宇智波帶土的死訊。
据說是同組的女忍親手做的眼部手術。帶土的尸体并未被帶回,那個叫做旗木卡卡西的少年,就那樣堂而皇之的回到了木葉。
他并不記得帶土的面孔,無論怎么回憶也沒有什么印象,那時听到消息心底唯一的念頭便是:
如果我是帶土的話。
如果我是帶土的話。
那是在每天都會經過的,從忍者學校回到家的路上。年幼的宇智波鼬垂著頭安靜的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和別的宇智波一樣穿著寬大的圓領上衣,團扇的標記緊緊的貼著他的后背,隨著他平穩的腳步微微的起伏著;空空的額頭被風吹過,他有時候會抬起頭來沉默的看著前方。
那條漫長的路上并不像十几年後那么的平整而寬闊,戰爭毀坏了一切,那路面坑坑洼洼,缺少修整和養護。
如果我是帶土的話。他想。
如果我是帶土的話。
白發的少年走過他的身旁,身后是宇智波家敞開的大門。
如果我是帶土的話。
他想。
我會把你們全部都殺掉。一個也不留。
那白發的少年有著如同烈火一樣顏色的左眼,額頭上帶著木葉忍者的頭帶,安靜的走過他的身旁,雙拳攥緊,微微顫抖。
如果我是帶土的話。
他想。
屬于我的東西。誰也別想從我這里拿走。
抬起頭時,赤紅眼瞳的顏色立刻就沉淀了下來,他仰望著那描繪著團扇圖案的厚重木門,明明是清澄的天空,可是卻襯得玄色的大門那么的肮臟又破舊。
那時他還未遇到止水。
那時他還只不過是眾多宇智波中的一個。
那時他還是父母唯一的孩子。
那時他還不知道故事會怎樣的展開。
直到垂著頭走過長輩身邊卻被輕松的捉住,他抬起頭,看到那個擁有最強寫輪眼的宇智波。
直到七個月後,那個名叫佐助的宇智波出生,他獨子的身份,從此消失不見。
他仍舊呆在保育院一般的忍者學校,每天照常回家,看著母親疼惜的抱著那個連降生都不會挑時候的孩子。
那時候,如同夏日午后突如其來的暴雨,村口突然有成片成片仿佛火焰般的紅花在匆忙的盛開,沿著遠去的路一直漫延到遠處天空消失不見的盡頭那里。
從警務部回到家里來的父親在母親偶爾提起的時候,仿佛若有所思般的接著說道那似乎是個好征兆。
他不知道父親到底是在說那些如火如荼般仿佛要燒盡一切的花朵,還是在說佐助的出生。
三個月後,仿佛是在嘲笑他的父親一樣,被九尾襲擊的木葉,以火影的死亡為代价,將九尾封印在了一個剛剪斷臍帶的嬰儿身体里。
那個封印著九尾的孩子名叫漩渦鳴人,也只不過是比佐助晚了三個月來到這世界而已。
鼬并沒有在四代目的葬禮上看到止水的身影,忍者學校的孩子們整齊的排著隊低著頭走上去,無論是男孩女孩都泣不成聲,他垂下了頭,把手中那支新摘的白菊擺了上去。
哭泣仿佛流疫一樣四處擴散著,葬禮上所有的人都在忙著落淚,他一個人在人群之中耐心的等待結束。
三天後,止水和自來也一同回到了村子,人們紛紛猜測著火影的重擔是不是要落在那男人的身上。
誰也沒想到的是:已經五十六歲的猿飛再次的走進了火影辦公室,而那時的自來也,早已經不知去向了。
大概就是在那場葬禮結束不久之后,止水從暗部退出,回到了宇智波家族所掌控的警務部。
那時他才知道,原來止水和死去的四代目同樣都是三忍之一自來也的弟子。
离開暗部進入警務部的止水,已經不再是那個帶著面具不為人知的地下忍者。很快的 ,那男人就被前輩們交口稱讚了起來,在他七歲從忍者學校畢前,止水已經被稱為是宇智波最強的男人了。
畢業之后鼬順利的成為了下忍,一如既往的枯燥和無趣,男人完全不曾過問這一切,似乎漠不關心。
一如兩年之前,父親對他說,三年後再說升中忍的事情吧。
那种好像是公事公辦一樣的口吻,父親那時嚴肅的坐在上座,命令他道。
心里的不快翻滾而起,他跪坐在那里,沒有抬起頭,想了想之后,也只是簡單的回答說知道了。
連續的跳級,然后無趣的在那個沉悶的地方多呆了兩年,這才終于可以离開,沒想到要面對的,是更加無趣的訓練。
要是我立刻就通過中忍考試會怎么樣?
那些,對他來說簡直易如反掌。
為什么會生出這樣的儿子呢?他甚至都不必抬頭。
父親心里的聲音那么的清晰。
如果控制不好的話,這孩子也許會……
如果抬起頭的話,几乎可以看到父親心底有根叫做鼬的弦在不斷的鉸緊。
鼬只是安靜的低著頭。
在佐助周歲之前母親一直留在家里,几乎沒有出過什么任務。所以每天見到母親的時間反而增多了許多。一開始這种狀況讓鼬有點茫然,但是面對鼬的時候看起來不知所措的似乎是母親。
最初他沒有搞清楚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只是努力的想把過去的那些維持下去,但是很快他就發現問題究竟出在了哪里。
終于忍不住的母親為難的問他說為什么都不看看弟弟呢?
正在包便當盒子的鼬停了下來,仔細的想了想似乎的确如此。
那時佐助已經過了滿月禮,總是哭泣的嬰儿讓母親夜里也不得安眠,他也曾經听到母親說這孩子和你一點儿也不象啊。
就算是這樣,說著佐助這孩子真是又粘人又愛哭的時候,母親眼睛里的笑容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鼬并不是有意忘記自己還有這么一個剛剛出生的弟弟。只是因為那哭聲實在讓人不愉快,所以他總是很少靠近抱著佐助的母親身旁。
鼬轉過身來,有些遲疑的伸出了手去,滿月過后那孩子變得白白嫩嫩的,他用指尖輕輕的触碰著那孩子的臉蛋,摸慣鐵器的皮膚似乎是頭一次接触到這么柔軟的東西,他的手指不自覺的抽了回來,看向母親的眼睛變得有些不自然。
母親居然笑了出來。
那是母親第一次在他的面前笑出聲來。
佐助一天天的長大,不知道什么時候就能夠伊伊呀呀的發出些奇怪的聲音叫喚著要東西了。每次鼬走過那孩子旁邊的時候,都會看到那張一無所知的臉傻乎乎的沖著他笑。
母親捉起那孩子的手朝他舉起,半玩笑半認真的哄著說:哥哥,叫哥哥。
嬰孩的手圓圓胖胖的,舉在半空中晃來晃去,他輕輕的攥住。那是如同他一樣漆黑的眼眸,他微微的低俯下頭,看到自己冷淡的面孔印在那雙清晰的瞳孔里,沒有絲毫的差錯。
他手里里小小的手指在輕輕的扭動著,那是仿佛雪片一樣的溫暖,不能久握。
佐助學會的第一個字眼是媽媽,然后就是哥哥。
第一次听到那聲音時他并不知道那是在叫自己,母親卻肯定的說是佐助在叫哥哥,疑惑的走了過去,于是看到那孩子的笑臉。
他摸著孩子的手,心里生出了微小的期望。
那天傍晚他第一次向止水提起自己的弟弟。
“那么……小……”他有些迷惑的站在湖邊,有點拘謹的用雙手比划著。“他只有這么一點……還會動……”
止水笑了起來,用力的揉著他的腦袋,愉快的將他的頭發揉得亂七八糟,“他會長得和你一樣大,那時候你看他就跟我現在看你一樣啊。”
他忽然屏住了呼吸,“……你把我當作弟弟嗎?”
他覺得手掌心里有微微滲出的汗。
“你真是奇怪的小孩。”止水斜著臉看著他笑了起來,但很快就恢复了冷淡的表情,“不過還是算了吧,不介意我說實話的話……我可是很討厭尊父哪。”
“沒關系,”他沒有絲毫遲疑的接過了止水的話,垂下眼看湖水中兩個人微微晃動著的倒影,“我也很討厭他。”
止水轉過臉來安靜的看著他,他突然覺的心里有些慌亂,但那男人也只不過是一言不發的看著他而已。
在警務部身居要職的父親,明明是那么的欣賞那男人。雖然鼬并不明白為什么男人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卻從來都沒有問過一個字。
“你知道我剛才想什么嗎?”男人終于開了口。
他看不出那人到底在想什么,沉默了一下,沒有回答。
“我居然看不出來你到底有沒有撒謊,” 男人站起身來,湊近了看著他的眼睛,很認真的對他說道,“你比我還适合暗部噯。”
那是止水第一次對他提起暗部。
走回家的路上,他猶豫著攤開了手掌心,慢慢的邊看邊走。那是清晰的簡直叫人害怕的掌紋,手心里干燥而溫暖,連一絲汗水的痕跡都沒有。
男人曾經捉住他的左手認真的看著,他奇怪到底能看出什么,男人卻說你是個淡薄的人啊。
他歪著腦袋。
男人呵呵的笑著,“說的不好听點呢,就是薄情的人哪。”
很少對他提起過去的男人,那天曾經對他說過。在途經云之國的時候,有一個看掌紋的女人說他命中注定會死在孩子手里。
“听到美濃的死信,我居然覺得好像松了口气似的。”止水笑著自嘲道,“沒有女人,就不會有孩子。我果然是個懦弱沒用的人哪。”
沒有想到止水居然會相信那种無常的事情,被松開左手的鼬凝神看了他几眼。
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一樣,止水冷淡的笑著說道:“因為她看著我的掌紋說我過去的事情,都差不多呢。”
鼬對止水的過去也知之不多。
身為孤儿,和四代目同為自來也的弟子,成為中忍后不久便進入暗部,期間的一切行蹤更是不得而知了。
止水的年代比起他所生活的現在要殘酷許多,直到几年后他進入暗部,還是很難想象少年那個乖僻的止水是如何變成如今這樣的。
那副開朗穩重的表象和冷漠陰沉的內里就好像冰与火一樣難以相容,但是無論是哪個止水,他都一樣的喜歡。
男人那看似溫柔的虛偽,成功的欺瞞了木葉所有的人,父親口中的止水,也是熱心族人事務的优秀忍者,絲毫沒有什么不好的評价。因為他和止水的親近,似乎讓父親寬心了許多的樣子。
最初鼬并沒有預期到會有類似于這樣的事情發生。
察覺到父親所想的同時,鼬只覺得深深的失望。
沉悶的味道,越來越濃,讓人厭惡。
和他同一年畢業的孩子,有兩個當年就通過了中忍考試脫离了下忍身份的。
雖然能夠完全按照老師的命令做事,但那种毫無來由的不耐煩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爆發,積聚在胸口的火焰沉悶的燃燒著,鼬就是在那時,從止水那里學會了龍火之術。
但是更多的時候,他只是毫無目的的跟在止水的身邊。在九尾襲擊村子前就要結婚的止水,因為未婚妻美濃死在那場悲劇中而至今單身,看起來似乎并不介意鼬的親近。
鼬經常面無表情的走進警務部的那棟樓,值班的警衛自然都認識他是部長的儿子,只是他通常是徑直的走進止水的那間辦公室,爬在桌子上看那男人認真的處理木葉的公務。
在宇智波滅族之前,警務部不僅管理木葉的治安和穩定,甚至還要協助暗部保衛村庄,那時鼬所看到的,就是整天忙于那些不分巨細的大小事件的止水。
從來沒有問過他到底來這里做什么的止水,有時候也會拿一些卷軸來問他,比起自己的回答,他更喜歡從止水那里听那男人偶爾無情且滿是惡意的評判,和那些寫了下來卻完全相反的字句。
但更多的時候 ,他從止水那里,什么也得不到。
盡管看起來并不介意他的親近,但從一開始,止水就沒在他面前扮演過親愛兄長的角色,一直以來,都是他默不作聲的跟在那男人的身后。
他總是被遺忘,然后在意想不到的時候听到止水的聲音。冷淡的男人也有隨性而孩子气的舉動,那些偶爾為之的親密,對于不懂得撒嬌或者任性的鼬來說,少得連一只手都數得過來。
呆在止水辦公室的時候,因為事務雜煩,有時候也會很晚才离開,止水在走出辦公室的那一刻經常是一臉的厭倦,但是在關掉燈走下樓梯時,厭煩而淡漠的表情便會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愉快的笑容,即便离開了警衛人員的視線,仍舊不會消退。
跟在止水身后离開的鼬,總是被那男人揉著腦袋,微笑著教訓說小孩子要有禮貌。
不一樣的只有那么一次。鼬八歲那年,大概是剛立秋的那天。傍晚跟隨著止水走出那棟樓的時候,止水曾停下腳步轉過身來指著警务部樓頂那醒目的标志問他說:
知道那是什么嗎?
火之团扇。他看著那東西心里這么想。
他回過頭看著止水回答說:宇智波一族的族徽。
男人露出了難以琢磨的笑容,突然雙手伸到了他的肋下,將他整個人高高的托起,然后穩穩的把他架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他怔怔的騎在男人結實的肩上,雙手被緊緊握住,心臟的跳動聲一下下的敲擊著他的耳膜。
“你叫什么?”男人突然問道。
他不加思索的回答說:“ 鼬。”
“笨蛋!”雖然看不到男人的臉,卻能听到那明顯的笑意。“你的姓呢?”
“鼬,宇智波 鼬,”他匆忙的回答道,好像遲一秒男人就會扔下他一個人走掉一樣。
他的鞋子隨著男人的腳步聲一下一下的踢在了那寬闊的胸膛上,他突然覺得羞恥起來,臉頰上燙得都不自然,緊張的看著那不平整的路面,心里不知道為什么愚蠢的擔心著止水會不會就這么不小心摔倒過去。
“我們來飛吧。”男人沿著他的手腕往上抓了抓,然后好像一個孩子一樣飛快的朝前面跑去了。
那是走回家的方向,他的胸口緊緊的貼著男人的腦袋,那深黑色的柔軟短發好像春天剛剛發芽一樣的草一樣,有种清爽的溫暖。
騎在男人的肩膀上時,周圍的一切突然陌生了起來,好像所有的東西突然沉入了大地,只要仰起頭就可以摸到天空似的,左側村口的方向有成片的紅花開得正盛,就好像夕陽下那燒遍了半個天空的赤紅色云霞一樣無邊無際的朝遠方舖去。
秋天的風總是把天空中所有的云都統統吹散,露出洁凈明朗的碧空來,即便是黃昏,所有的云也全部都被拉了下來,打著褶子漂亮的堆積在天際線上,空气里的味道干爽而清新,道路上的風,傻呼呼的貼近過來,溫柔的把他的頭發吹的飛了起來。
有時他會夢到這里。夢里,止水把他架在肩膀上,安靜的一直朝前走,他們走在那如同云彩一樣的紅花旁,小小的木葉里那些拳頭大的紅花狂暴而沉默,淹沒了空無一人的村庄。止水仿佛要永遠那么走下去似的,身邊有星子般發著微光的小虫嚶嚶的飛舞著,他靜靜的呼吸著,任憑男人抓緊了他的手腕。
所有的一切都被那火焰般的紅花深深的埋葬了,所有的一切都從那個腐爛沉悶的世界消失不見了,他夢里的木葉,鮮艷安靜,繁盛茁壯。
在夢里,那漫長的路沒有盡頭,他一次次的夢到那些宛如染著鮮血的指骨的花瓣,被安然前行的止水踏在腳下,那些微微晃動的紅花,仿佛無數雙從地獄伸出的白骨, 好像要將他們一同拉入那幽冥地獄一樣的揮動著,那些沾染著血跡的手指匆匆的擦過止水的腿,卻總是拉不住。
在夢里, 他彎下了身体,腦袋緊緊的貼著止水的側臉,听著男人平靜的呼吸和心跳聲,男人的身上有腳下紅花的淡淡味道,一切都那么好,清澈安靜,空曠完整。
后來,十五歲的鼬,一個人走進了曉那迷宮般的居所深處。夕陽那血紅色的光彩從大地上退盡之后,小小的和室里滿是月光,黑底紅花的被褥打開時有雪的味道,那一晚他夢到止水,和過往的哪次都不一樣。
夢里他只有七歲,孤身一人,踏過那汪洋一般的紅花,在那遙遠的黃泉路上安然前行,火照之路的盡頭,有那男人疲憊的側影。
男人冷漠而不快的說怎么這么遲。
他想了想。
還未來得及開口,便醒了過來。
他坐在那里看著紙門上微微晃動的樹影,再一次清晰的想起了男人早已死去的事情。
即使是在夢中,遠方的路口也模糊得如同霧一般,如果還未醒的話,他大概會恩一聲,然后跟在男人的身后,安靜的朝前走吧。
死去男人的愿望那么的簡單,十四歲的鼬听得一清二楚。只是死去的男人不知道,對于滅族的 宇智波,他的心愿已經沒有了絲毫的意義。
同那云之國的女人所預言的一樣, 宇智波家的止水在三十歲的時候离開了這世界。
死于孩子之手。
而那時騎在男人肩上望著遠處盛開著紅花的小路的鼬,并不知道男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所圖謀的。
只是他內心中隱隱的察覺到,那男人是同他一樣的人,胸口都有安靜的野獸蟄伏,不知何日才能將其喚醒。
也許那男人所作的一切,就是為了要將名叫鼬的獸喚醒吧,把那只會帶來厄運的獸,從宇智波那陳腐而瀕死的体內喚醒,教他睜開雙眼,教他如何使用利爪和尖牙,教他學會依賴,指給他獵物的方向,給他強大的力量,讓他代替自己實現那深埋心底的愿望。
即便如此,他還是跟在那男人的身后。
那男人的心也在慢慢的死去,但卻帶著新雪的味道,那种覆蓋了一切的冷漠和隔絕感讓他深深的依戀。
那男人看著他慢慢的強大起來,等待著鼬來完整那個云之國女人的預言,等待著一切結束,等待著他弱小的希望可以成長,等待著他成為鼬最重要最親密的人的那一天。
而年幼的鼬,那時當然還不知道,當他跟在止水身后時,他未來的人生之路就已經舖滿了秋天的紅花,那條血染之路,注定要指引他通往幽冥之地。
年幼的鼬,只記得止水是如何的把他帶回了家,只記得那男人是如何在那沉重而高大的木門前把他放了下來,只記得他是如何失望的跟在男人的身后走了進去。
在經過叔叔嬸嬸那里的時候,止水揉著他的腦袋朝他們問好。那是那男人虛偽的一面。
奇怪的是那時候他連這一點都喜歡。平時明明會低著頭沉默的走開,那天卻抬起頭來看向了對方,止水輕輕的拍了一下他的后背:“小孩子要有禮貌。”
他好像被催眠了一樣,老實的問著好。
也許無論那男人說什么他都會照做吧,那時候的鼬,并沒有覺得有什么不對。他完全的忘記了,那男人是族人派來監視他的。
一開始嘲笑過他是個笨蛋的止水,也會稱讚他异于常人的意志力和清醒的頭腦,后來便有那么一次說到過他很适合去暗部的話。
“去看一些你平時看不到的東西吧。”男人那時是這么說的。“或者看看……你平時看到的那些東西,是不是你所看到的那樣,是不是你所想的那樣。”
男人說那話的時候他剛通過中忍考試,因此他不是沒有怀疑過男人的意圖。但是……對于那時的鼬來說,無論男人讓他做什么他都會毫不猶豫的照做啊。
雖然那男人從來沒有吩咐過他什么。
通過中忍考試后父親要他為進警務部做准備時他回答說他將進入暗部,父親臉上吃惊的表情多過憤怒。
不知道是因為他不再沉默還是因為他拒絕了父親的決定。
离開的時候在走廊上遇到了莽莽撞撞跑過來的佐助,那孩子走路根本不看前面,結果一下子的扑到了他的身上 。
年幼的弟弟什么都不懂得,只會象影子一樣的粘在他的身旁,用那种小孩子的口吻任性的撒著嬌,叫著哥哥的時候仰起頭來,還帶著淺淺的鼻音。
那個五歲的孩子其實已經會抓著苦無朝著靶心投擲了,只是正中紅心的几率實在低到了可怜的地步,曾經看到那孩子練習情景的鼬站在房檐的陰影里實在是說不出那時自己心里的失望由何而來。
佐助是個情緒明顯的孩子,不論是喜怒哀樂都清楚明白的寫在臉上。戰爭年代上忍還有中忍都任務繁重,木葉村里經常處于人手不太夠用的境地,七歲時成為下忍的鼬也開始頻繁的出任務,幼小的佐助每次听到他對父親說起第二天要出任務的話就會變得不高興起來,用筷子不滿的戳著米飯,不愿吃飯。
那孩子完全和他不象。不喜歡納豆,愛吃番茄,淘气起來一點都安靜不下來,很小的時候就會問好會羞澀的笑,會用那种期待的眼神看著他,問著哥哥什么時候才會回來,會用那种夸張的表情和口气說哥哥超級厲害的,然后撒嬌般的央求他要他教自己手里劍。
最初他不太懂得如何應付那孩子,剛學會說話時的佐助還好打發,但是再大一點他就不知道要如何是好了。
那雙看著自己的眼睛里充滿了毫無警戒的信任,他看著那副与自己相似的面孔,只覺得生疏。在玄關處坐下來換鞋子的時候,那孩子經常追出來認真的對他說哥哥要早點回來。
有時候他就坐在那里,看著小小的佐助站在他的面前。
他想了想,自己是不是應該象止水那樣伸出手來揉揉那孩子的頭發。
但還是沒有,他只是伸出手,用兩根指頭戳著佐助那尚未用頭帶保護起來的額頭,看著那孩子踉踉蹌蹌的朝後退去,退了四五步這才站穩。
佐助抬起頭來看向他的時候,额头正中已经微微的发青了。
他叫着佐助,那孩子撅着嘴,雖然看起來很不高興卻還是听話的走了過來,并沒有因此而變得警惕起來。
那年幼而愚蠢的弟弟完全不知道。
戰場上,站在他面前的人只需要再大些力气就可以殺掉一個人了。
“傻弟弟啊……”
那孩子用手背揉著額頭,不滿的嘟囔著類似于哥哥真討厭這樣的話。卻在他起身离開時匆忙的穿了鞋子追出來,著急的重复著之前說過的話,抓住了他的衣袖要他早一點回家。
他什么也沒有回答。
如果這就是父親想要的……
他想。
那么……自己也沒有任何期待的必要了吧。
在進入暗部之前,父親曾經又找他談過一次話。
大致的意思還是要他准備几年后直接進入警務部。
他不知道那是不是父親身為警務部部長的職責使然。
他沉默著,父親等待了很久等不到他的回答,最后只是說,我真搞不懂你這孩子在想什么。既然你那么親近止水,為什么不想來警務部呢?
那是第一次,他從父親的口吻中听到妥協和疲憊的聲音。
他抬起頭來看向端正的坐在他面前的父親,不無嘲諷的想著,您什么都不知道啊。
沒有人知道真正的止水在想什么,那時鼬以為自己知道。
雖然沒有明白的說出口,但是止水的失望就好比清澈河水下密如星子的砂石一看便知在,他的面前絲毫沒有掩飾。
鼬中忍考試結束后去止水的辦公室,看著止水身后的牆壁上那些永遠都無法開口講話的宇智波,那些歷代的警務部精英們同樣低著頭注視著他一樣,只是那表情看起來仿佛有什么難言之語似的。
“警务部啊……”察覺到鼬的目光之后止水回過了頭,仰望著自己身后那些陳列了几十年的畫像,“宇智波的先輩們,看到現在的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憤怒的從冥河那邊沖過來。”
鼬看向止水平靜的側臉,不太确定對方到底是不是在開玩笑。
說話的男人其實并沒有回過頭來,不過鼬還是知道他開始生气了,雖然說話的時候好像在笑一樣。
“現在的那些宇智波啊,好像被拔掉毛的鷹一樣,連看家都看不了。”
說完這話止水就轉了回來,攤開要看的卷軸,垂下了頭,黑色的眼睛,深深的埋藏在濃密的陰影之中。
他十歲時順利升為中忍后,當年便進入暗部。止水在看到他的白色面具之后笑了起來,問他說那是什么。
他沉默了一下,回答說是ITACHI(鼬)。
止水只是揉了揉他的頭。
的确, 鼬只不過是一种會帶來厄運的獸。
可惜他并不是止水,會在乎那些命運無常的荒唐說法。 他背負著這個名字平安無事的活了十年,至今無恙無災,即便那古老的說法是真的,也應當是他給別人帶來厄運吧。
但是隔天再見到止水的時候,鼬的手被抓住然后用力的掰開了。
“十歲就進暗部,年紀還是有點小,”止水把一樣東西放在他的手心,“一半靠實力,一半靠運气吧。”
那是粗糙而簡單的黑色鏈繩,上面均勻的系著三顆淡棕色的石頭圓環。止水給他這樣的東西,也許是因為圓環石能夠消解厄運的說法吧。
那是他從止水那里得到的唯一一樣東西。
只是那時,誰也無法預言未來。
后來想想,也許對那男人來說,這种無處不在的細微巧合,也許正在悄悄的向他宣告著他的未來。 親手終結他性命的孩子,就是四年前從他手里接過那鏈繩的鼬。云之國的女人,不止說對了他的過去,還誠實的描繪出了他的死亡。
那年立秋時,村口的紅花就安靜的綻放了,把鏈繩放在胸口位置的鼬,跟隨著暗部成員第一次外出執行任務,地點遠在云之國。
歸來的那天,佐助在村口等著他,開始還以為是情報泄漏的鼬,后來才直到是年幼的弟弟天天都在那個位置等待著他的歸來。
雖然告訴過那孩子不要再做這樣的事,但是那任性的孩子完全不听他的話,佐助頑固的時候,倒是和他很像。
進入暗部后鼬找到了一個避開家族事務的借口。直屬于火影的暗部成員們沒有固定的行蹤,任務也完全是机密,絕不公開。
佐助希望他教他手里劍,但總是被他以有任務的借口推掉了。离開的時候,那孩子臉上的失望,他不是沒有看到。
那孩子總是有种天真又愚蠢的期待,鼬不知道為什么那么多次的拒絕后他還是任性而又一如既往的跑到自己的身邊來,撒嬌般的要求著自己去教他手里劍。
只要喊他的名字,就會听話的跑到他身邊來的佐助,似乎總也不長教訓,沒有頭帶保護的額頭,每次都被他用手指戳得青了起來。
“傻弟弟啊……”
佐助跟在他的身后,揉著額頭,一步也不放松。
他停了下來,看著那張和自己相似的臉,想著……也許止水就是這么的看著自己的吧。
于是,他漸漸的忘記了自己曾經的失望。
十三歲,鼬成為暗部分隊長。
父親知道后并沒說什么,其實自從他進入暗部之后,父子之間便极少說話了。如果說之前還因為止水的緣故對他有所期望的話,那么現在看來,父親似乎是打算徹底放棄他了。
只是,雖然不喜歡自己,卻又免不了拿佐助和自己做比較的父親,還有那么任性的粘著自己的佐助,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更同情哪個一個。
是生長在自己的陰影下的佐助,還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父親。
資質遠不如鼬的佐助,比他想象的還要努力。鼬不知道這個流著和他相同血液的孩子,究竟能不能超過他,能不能讓他用性命去保護。
也許他會親手殺死佐助然后离開這里吧,也許不會。在那一天沒有來臨之前,鼬也不知道一切會不會有所改變。
他以為他仍舊有耐心,可以安靜而沉默的等待,如同過去的那十四年,行走在這個日漸死亡的家族之中,壓制著胸口的野獸,裝作什么都不會發生的樣子。
但是止水親手結束了這一切。
止水一直是那么的了解他。
將族人捆綁起來拴在木葉腳下的宇智波啊, 用寫輪眼的尊嚴來交換權力和地位的宇智波們啊,這里發生的所有一切在他看起來簡直令人痛恨。
那男人對鼬說,對那個一直渴望強大,緊跟在他身后的鼬說:
“你已經很強了,難道不想變得更強大嗎?”
剛執行完S級任務歸來的鼬,在止水那熟悉的辦公室里听到這樣的問話后,抬起臉來看著那男人熟悉的側臉。
“你知道什么叫做万花筒寫輪眼嗎?”男人抬起手,示意他走到他身邊去。
他想了想,安靜的走了過去。
十四歲時,鼬仍舊還是個孩子,站在那里也只不過勉強能平視著男人的眼睛。
“我想讓你得到那雙眼,”男人坐在平時所坐的位置上,合起了桌上原本攤開的卷軸,用一种從未有過的溫柔聲音對他說道,“你覺得怎么樣呢?”
他覺察出有些什么不對。
但他一無所知。
“怎么得到?”他簡短的問道。
男人露出了疲憊的笑容,用右手的指腹輕輕的摩娑著脖頸,安靜的問他道,“鼬,你最親密,最重要的人是誰?”
他微微的皺起了眉頭,抿住了嘴巴。
男人用食指的指節慢慢的蹭著下巴,想了一下,換了一种說法,“比如說,如果我想得到万花筒寫輪眼的話……我只需要殺掉我最重要的人就行了。”
他沒說話,窗外的天空暗了下來,他記得父親說過,今晚是族内集会的日子。
“不過可惜的是……一個也沒有……木葉也好,宇智波也好,都是些讓人討厭的家伙啊。”
他看著男人冷淡的眼睛,覺得手心里突然潮濕了起來。
“要是我也能象老師那樣堂而皇之的逃跑就好了,”止水的聲音漸漸變低,冷笑的看著他,他的胸口起伏著,男人的右手伸向了他的脖頸,慢慢的圈緊,他沒有躲避。
“不是你的父親吧,”男人肯定的看著他,繼續平靜的問了下去,“是你的母親嗎?”男人手上的力气漸漸變大,“是你的弟弟嗎?”他安靜的呼吸著,一直看著男人的雙眼,“是我嗎?”
有那么一瞬間,他以為他忘記了呼吸。
止水露出了愉快又疲累的表情,把最后那句話又重复的問了一次,“真的是我嗎?”
他開了口,与此同時,男人的手輕輕的松開了。
“今晚有集會,你要參加。”
“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万花筒寫輪眼, 鼬,”男人伸出了手,揉亂了他的頭發。“我對如今的宇智波一族,已經失望透頂了。我想給你万花筒寫輪眼, 作為交換,你來替我清理這腐爛的家族吧。”
他緊緊的閉著嘴巴,一言不發。
那時大約是剛立秋,佐助的生日過了沒多久,村外的紅花再次舖滿了小路,他跟在男人的身后,走在淺淺的河堤旁。夕陽已經落山了,完全暗下來的天空盡頭,被撕得絲絲縷縷的云彩后仍舊有些微弱的紅光。
連遺書都寫好的男人,微笑的說起了云之國那個女人的預言,心意已決的止水,對他說的最后一句話,讓他下定了決心。
“我會在黃泉路的那頭等著你喔 ,鼬。”止水露出了孩子一樣的笑容,毫不在意的站在了他的面前。
到了最后,除了那條黑色的鏈繩,男人什么也沒留給他。
那一整夜,他的雙瞳赤紅如血,無法消退。
几天后,村里的族人在河底撈起了止水的尸体,鼬在庭院里受到族人的盤問,他心底的野獸凶猛而憤怒,一触即發。 只是那時他還未能完全控制那雙眼。
愚蠢的族人,完全不知道事實的真相只是一昧的猜疑。 只知道守在原地不動,卻不知道這世上的事不能只看表象,也不能只凭想象。
那時鼬還不知道,除了他自己,這世上還有另外一雙万花筒寫輪眼。
那一年,止水三十歲, 鼬十四歲。
那一年,宇智波全族覆滅。
男人的心愿以一种极端的形式達成了, 所有的人都死了,宇智波一族只剩下了三個人。
他不知道將來該要如何面對黃泉路那頭的男人。 只是鼬知道,只要他還活著,這世上,永遠都不會再有人揉著他的頭對他說小孩子要有禮貌的話了。
和他有著同樣万花筒寫輪眼的男人也离開了木葉。
那小小的村庄里只留下了他年僅九歲的弟弟佐助。那年幼的孩子心怀著仇恨和絕望,孤獨的活在過去的陰影里。
他仍舊記得滅族的那一晚,那孩子狂亂的奔逃和痛哭流涕的哀求,求他不要殺掉他,求他放過他。
他不知道止水有沒有騙他。
就是這樣懦弱而無用的弟弟,會和他一樣,擁有万花筒寫輪眼的資質嗎?
他知道那孩子是多么的崇敬他,喜愛他,如果佐助殺了他,就可以得到万花筒寫輪眼,他等待著那一天。
“愚蠢的弟弟啊,如果想殺我的話,那就憎恨吧。”
他在那暗紅色的月讀空間里看著那個抱著頭痛哭的孩子,冷淡的說道。
對于那個生長在母親溺愛下的膽小鬼,也許只有憎恨才能給予他力量吧。
他望著那狂亂的孩子,耐心的等待著,只是他從來都沒有明白過。
這世上再也不會有第二個鼬了。
他也永遠不可能成為第二個止水。他永遠不是止水,就算擁有了和那男人一樣的掌紋。
他那懦弱愚蠢的弟弟也許永遠都不可能是那個會將他殺死的孩子。
但他仍舊固執而安靜的等待著,等待著那孩子慢慢強大起來,等待著那孩子得到万花筒寫輪眼,將他殺死的那一天。
當鼬三年后再次見到佐助時,他輕易的折斷了那孩子的手臂,那愚蠢的弟弟啊,甚至連反抗都做不到。
他想也許止水錯了。
那孩子那么絕望而憤恨的看著他,仿佛他們之間根本沒有那三年的間隔,仿佛那小小旅館的二樓是宇智波家族那些遍布著血跡的庭院,那里到處是族人的尸体,那時已是傍晚,夜色低沉, 紙門拉開,月光涌入,所有的一切明亮純白,罪証清晰,他那幼小弟弟的憎恨和恐懼淹沒在他一手做出來的月讀空間里,悄無聲息。 只是他那愚蠢的弟弟,那淺薄的恨意仍舊是不夠啊。
不夠得到万花筒寫輪眼,不夠殺了他,不夠結束這一切。
三年的時候也許還是太短。止水等了他十年,至少他還可以再等。
鼬并不知道,他那個愚蠢的弟弟,是怀著怎樣的心情,一步步的走進了重疊的深林之中。 少年的夢里,那條舖滿紅花的路上,有他溫柔的背影。
佐助的确沒有走那條鼬曾走過的彎路,那是因為他親手給那孩子指出了另外一條崎嶇的道路。
而鼬,仍舊耐心的等待著。
在那暗紅色的月讀里,那紅花常盛常開,永遠鮮艷,葉出未逢花,花開不見葉,花葉永不見,一年一春秋,生生世世兩相隔。
在他的夢里,他仍舊是孤身一人,在秋風里踏過那汪洋一般的紅花,在那遙遠的黃泉路上安然前行。
火照之路的盡頭,有那男人疲憊的側影。
就算那里是地獄, 就算男人會責問他為何看著宇智波全族覆滅,就算男人已經走過了忘川忘記了關于他的一切……
他還是要回到他身邊,戴著那黑色的鏈繩,帶著那雙万花筒寫輪眼,帶著那過去一切的回憶。
他會保護他,如同許多年前那男人保護著他,他會捉緊他的手,一如許多年前那男人捉住他的手,他會走在那男人的身后,就如同那人的影子,步步緊逼,不再离開。
鼬在夢里所渴望的一切,要在遙遠的未來才能實現。
在那遙遠未來的路途上,舖滿了鮮血。流淌在他身后的,是全族之血,而在將來的某一天,他將會被一個宇智波的孩子殺死,用自己的血,染紅他眼前的路。
在那條血染之路上,只有他一人。
路的盡頭,有那死去的男人和那生在彼岸的紅花。 在等待著他。
-F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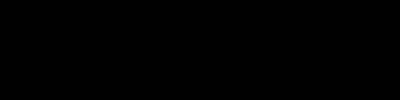

 ABOUT ME
ABOUT M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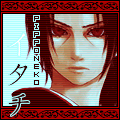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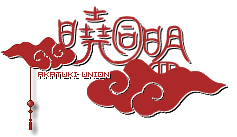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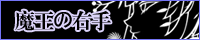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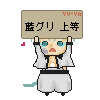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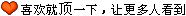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